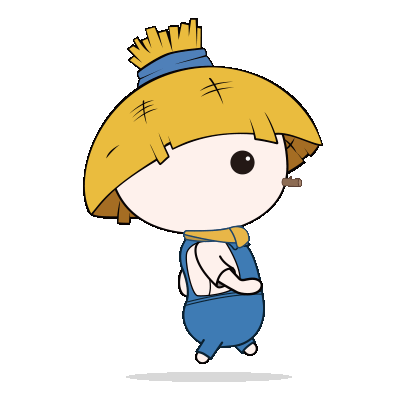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主子,窗台上的红梅该换了。”一大清早,巧兰特意跑去梅园,折回一束裹着白雪的红梅枝子,笑着朝主子邀功。
“不必。”
傅玉筝站在书桌前作画,头也不抬,语气偏淡。
巧兰一愣,花瓶里那束都蔫吧了,还不换?
巧梅知道原委,再蔫吧也是山麓书院采回来的战利品,主子哪舍得丢弃?
巧梅贴心地备上花剪和洒水壶。
果然,傅玉筝画完画,便手执花剪,“咔嚓咔嚓”,心情愉快地修剪红梅,去掉蔫吧的花叶,留下精神抖擞的。
一刻钟后,迎来了缩小版的花束。
依然红灿灿的动人。
“主子手真巧。”巧梅真诚夸赞。
巧兰心里微凉,不知从何时起,主子待她远不如巧梅热络。
明明她俩都是大丫鬟,都是七岁就追随主子的!
十七岁的巧兰,忍不住躲去园子一角哭泣。
恰好,蒙着面纱的傅玉瑶路过:“这不是三妹妹身边的巧兰吗?好端端的,受委屈了?”
傅玉瑶心知巧兰是傅玉筝心腹,轻轻搀扶她起来,体贴地劝慰:“人活在世,哪有没灾没难,不受委屈的。”
巧兰知道自家主子与大姑娘不睦,避嫌地拉开距离。
傅玉瑶毫不在意,收买人心不急于一刻,从手腕上褪下一个手串,赏她:“好丫头,别哭了。拿去换银子,买点好吃的犒劳自己。”
说罢,傅玉瑶不再纠缠,转身朝傅玉筝的桃花院来。
一进里屋,窗台上鲜艳的红梅扑入眼帘,傅玉瑶找话寒暄:“三妹妹娇养的红梅真喜庆,好看。”
傅玉筝笑:“当然喜庆,前几日山麓书院摘的,特意带回来娇养,留作纪念。”
傅玉瑶:……
一个寒颤。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她就是在山麓书院毁的容!
傅玉筝当然知道,否则也不会提啊。
说话嘛,本就是门艺术,怎么能戳痛堂姐的心,就怎么说。
“大姐姐,不好好躲在房里养脸,过来何事?”傅玉筝坐在临窗暖榻上描花样子,边描边问。
看都不看傅玉瑶一眼,更甭提上茶看座。
备受冷遇的傅玉瑶,也不敢闹情绪,她可是来求人的。
“三妹妹,雪肤膏用完了,你能不能让大伯进宫一趟?”
“进宫作甚?”
傅玉瑶急忙道:“求皇上再赏赐一瓶。”
傅玉筝好似听到了笑话。
搁下画笔抬眸睨她:“哦,雪肤膏轻易不赏人,除非对方对国家对社稷做出过重大贡献。”
“不知大姐姐有何功绩?”
傅玉瑶:……
她一个深闺少女能有啥功绩?
傅玉筝又问:“你没有,那你爹爹和两个哥哥呢?”
傅玉瑶:……
真是一脸的尴尬,她们二房什么样她又不是不知,还问什么问啊?
不是专踩人痛处么。
呵,傅玉筝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你一家子什么功绩都没有,还妄图皇上赏赐?岂非白日做梦?”
“巧梅,送客。”
傅玉瑶:……
“三妹妹,我父兄无,可你爹爹有啊。大伯父常年驻守西陲,保家卫国,乃国之栋梁,只要大伯父肯进宫讨赏,一定能要回雪肤膏的……”
“再不济,三妹妹,你去求求锦衣卫指挥使高镍,看在你的面子上,高大人一定会帮忙的……”
“他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什么都能求的来……”
闻言,傅玉筝冷笑。
又是指派她爹爹,又是点名高镍。
如此大言不惭,傅玉瑶是怎么有脸说出口的?
真当她是香饽饽,全天下男人都该围着她转?
呸!
示意两个粗壮婆子架起傅玉瑶就往外拖,呼叫声越听越小,直到被丢出桃花院大门外,终于耳根子清净了。
傅玉筝放她进来,主要是想一睹她的疤脸恢复得如何了,如今已经看到,疤痕剥落,留下淡淡的印记。
虽然淡,但胜在量多。
纵横交错,像极了浅色蜘蛛网。
纵使蒙着粉色面纱,露在外头的眼角和额头也怪……骇人的。
不知道,这样“容貌奇特”的傅玉瑶,高晏还爱不爱呢?
~
傅玉瑶被丢出去后,又跑去哀求大伯母陶樱,甚至跪在大伯父靖阳侯下值的必经之路上,折腾了整整一日,却毫无收获。
“亏我日日喊你们大伯母,大伯父!”
“……什么血脉亲情?全是狗屁!”
“一群冷心冷情的玩意!”
傅玉瑶疯起来,破口大骂!
骂着骂着,又对着梳妆镜里“美貌不再”的自己,大声恸哭。
二太太乔氏听到哭声,进来搂住女儿,两人一块抱头痛哭。
“我的女儿,你命真惨啊。”
“都是傅玉筝一家子害的,他们见死不救,他们冷血,他们不是人!”傅玉瑶趴在乔氏怀里,咬牙切齿。
四姑娘傅玉萱住在稍远些的小轩里,听到亲姐姐不住地叫骂,心烦,便过来支招:
“姐,别哭了,省省力气写封求助信,让高晏帮帮你,比啥都管用。”
高晏的镇国公府,肯定不缺雪肤膏。
不提高晏还好,一提傅玉瑶哭得更绝望了:“他、他已经不搭理我了……”
乔氏大惊:“怎么?”
傅玉萱也一怔:“什么?”
傅玉瑶哭哭啼啼叙述,原来使用雪肤膏的当日,她就给高晏去了求助信,几日过去,音信全无。
“一定是那日见我容貌被毁,他起了嫌弃之心。”
傅玉瑶越哭越伤心。
傅玉萱却是心头一松:“我当什么事呢,只是没回音而已。姐,你且放宽心,八成是她娘管控严格,高晏找不着机会回信罢了。不算事。”
傅玉瑶心头一喜:“当真?”
傅玉萱很肯定地点头:“你耐心等待便是。”
患得患失的傅玉瑶,又破涕为笑。
看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女儿,乔氏辛酸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