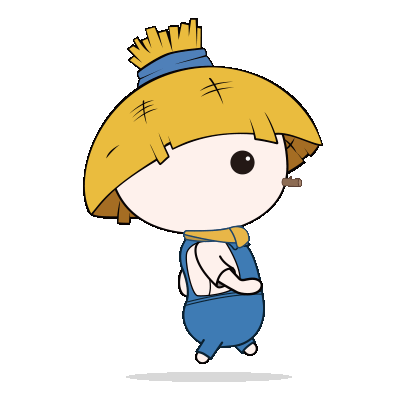王青阳见奉常寺众纷纷爬起,相互搀扶着,虽然狼狈,倒不曾死掉一人,心中略宽,对陈玄丘道:“陈大夫,我奉常寺今日这般情况,可是不能再招待你了。”
陈玄丘目的已达,一瞧人家下逐客令了,马上爽快答道:“好说,好说,你们且好好养伤,陈某改日再来。”
王青阳额头青筋绷了一下,呲着牙向他一笑。
无名使一手缩地成寸术,身影闪烁着追到神殿前,恰见陈玄丘向王青阳等人拱拱手,收了宝葫芦,施施然向外走,连忙快步追了上去。
王青阳已悻悻转身,转身之际虽然眼角梢到了有道人影一闪,却也并未在意。
小无名真是来去自如,自始至终不曾被人拦下询问他半句。
安知命走到王青阳身边,气愤地道:“陈玄丘此去,必然张扬其事,败坏我奉常寺声名。”
王青阳淡淡地道:“不然又如何?留下他么?我奉常寺,这是下定决心要和雍王决裂了么?”
安知命语气一窒。
王青阳挥了挥衣袖,道:“收拾一下,伤重者好生治疗。”
王青阳说罢,便纵身掠过神殿,宫门轰然关闭。
王青阳越过宫殿中巨大而空旷的空间,飞抵那云床之上,身形一落,哇地一声,一口鲜便喷了出去。
他是负责操控镇魔鼎的人,所以受到的伤也最重,方才在众人面前只是强作镇定罢了。这就是借法的缺点,自身除了意志力,其他方面并不强大,一旦来不及借法护身,防御力非常弱。
王青阳喘息着从袖中摸出一方手帕,轻轻拭了拭唇边鲜血,沉声道:“出来吧!”
一道白影一闪,屏风后面闪出一道人影,落在了王青阳的面前。
白衣如雪,黑发如墨,杏眼桃腮,明眸皓齿,瞧来既清纯又美丽,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气质,仿佛一眼幽泉所化的精灵,给人一种无比涓净、透明的感觉。
来人正是妲己。
天狐九尾,亦有九变。其中第一变,就是化形为人。
现在妲己只生出一尾,除了本体狐身,只能化为人形。
之前她对陈玄丘动手时,竖瞳兽耳,其实仍是妖兽形态,算不得化人,此时才是她的化人形态。
“主人,你受伤了!”
妲己很惊讶,奉常寺的太祝,是天神在人间最大的代言人,可以借用种种强大神通。
而且他如今身在奉常寺内,在他的地盘上,有种种阵法加持,人间有什么人能伤到他?
妲己却不知道,伤了王青阳的,正是天上至纯至阳至刚至正的九宵神雷。
王青阳淡淡一笑,道:“不妨事。妲己,老夫交给你一个任务。”
妲己欠身道:“请主人吩咐。”
王青阳神色一厉,沉声道:“老夫知道,你一直嫌弃林中寂寞,想要出去,但你年纪还小,道行未成,老夫放心不下,所以一直禁你的足。不过,现在老夫改变主意了!”
妲己神色一喜,“扑愣”一下,一条雪白的毛绒绒的大尾巴就从身后弹了出来,在她屁股后面风车似的摇啊摇。
王青阳瞪了妲己一眼,妲己赶紧伸手掩在臀后,按住了兴奋难捺的大尾巴。
可是,她的一双尖尖的长绒毛的兽耳,又嗖地一下窜了出来。
王青阳摇头叹道:“老夫的道行神通来自借法,所以心志越是纯粹坚定,力量越是强大。而除了我奉常寺一脉,世人都是修习自身的力量。对他们而言,修行就是历练,坐而论道是难成正果的。
你所修习,也是一样,需要入世历练,否则光是一个心境方面,就永远难以成熟。你是该入世了。但是,你这样沉不住气可不成啊,喜怒形于色,很容易就会被人……”
他还没有说完,妲己生怕主人改变主意不让她出去了,忙道:“不会呀,这是因为在主人身边,所以人家不需要掩饰,也生不出戒心,如果出去了,哼,我就不信,斗智会输给任何人。”
王青阳方才确实动摇了念头,但是听她这一说,似乎也有道理。天狐一脉天生慧黠,怎么会傻傻的轻易被人识破?
想到这里,王青阳展颜道:“好,既如此,那老夫就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就离开,追上陈玄丘。
此人道行神通,老夫现在也猜度不透,你不要急着下手,可以想办法先接近他,摸清了他的底细,再趁其无备,动手杀了他。”
妲己一听可以出去玩了,顿时喜上眉梢,大尾巴又摇了几下,雀跃地道:“好。”
王青阳神色一肃,道:“你记住,你离开期间,唯一的任务,就是杀掉陈玄丘。其他任何事,完全不必站在老夫的立场上,一切以取信陈玄丘为要,以免露出破绽。”
“是!”
“在此期间,但凭你便宜行事,但有一点,如果你不慎暴露了身份……,无论如何,不可承认你是出自奉常寺,不可说出老夫来!”
妲己一对尖尖的兽耳弹动了一下,道:“是!”
王青阳拂袖道:“去吧!”
妲己翩然一闪,化作一缕青烟不见了。
两只巨大的铜鹤,却仍在喷吐着袅袅的檀香烟气。
王青阳缓缓抬起头,望着那袅袅升起的香烟,喃喃自语道:“此人难道竟是来自上界?否则,那道神雷,万万没有突然转向的道理。还有,他那只可大可小的紫皮葫芦,似乎与姜飞熊的宝葫芦同出一脉。
可是,如果他是来自上界,为何要与我为敌呢?难道他不知道我是……,还是说,上界神明之间有了分岐?”
王青阳沉吟良久,目中露出一抹狠色:“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想挡我的大道,我就只能除掉你,别无选择!”
……
小巷里,龅牙、发量稀疏、眼睛也小的阿花,正蹲在溪水边捶打着衣服。
一个瘦小、憨厚的布衣男子站在她身后,倾诉着绵绵情话:“阿花,看到你的第一眼,俺就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俺知道,俺再也不能忘记你了。不知多少个夜晚,俺一遍遍地念着你的名字,烙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花花,俺喜欢你……”
阿花撇撇嘴,捶打衣服的力道更重了,就像是一棍棍锤在那个男人身上。
她是很丑,可这世上只有打光棍的男儿,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
只要她愿意,总有个丈夫可嫁,谁会选这个人呢?
好吃懒作,嗜赌好酒,他上一任婆娘,就是被他酗酒殴打后含泪上吊的。
“卟嗵!”一道人影突然从阿花背后扑过来,一头砸进了小溪,溅了阿花一脸水珠。
哎呀,这人真是无赖,居然用投河这一招逼她。
你有本事你投大河么,这里的溪水才及膝,能淹死人么?
咦?他怎么不动?难道摔晕过去了,滥赌鬼的身子果然虚得很。
阿花正想着,背后传来一个清丽悦耳的声音:“你,站起来!”
阿花一回头,顿时有种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的感觉,眼前一亮。
一个恍惚,阿花手中的捶衣棒就砸到了脚面上。
面前这个白衣小姑娘真是好美好美,仙气飘飘。
她真是踩在地面上了么?为什么她赤着一对秀气的小脚丫,一路走来,却涓净白皙,纤尘不染?
白衣姑娘上下打量了一番,评估了一下阿花的高矮胖瘦,满意地点点头:“就是你了,女人,脱衣服!”
阿花大惊失色,立即双手抱胸,颤声问道:“你,你要干什么?”
小仙女儿摊开晶莹欲透的一只柔荑,娇嫩的掌心摊着十粒黄澄澄的金豆子。
小仙女儿道:“脱,金豆子就归你。”
阿花两眼一亮:“是你说的,不许失言。”
阿花立即一扯腰带,就去解青裳的系扣儿,动作麻利无比。
“停停停,我只要外衣,你不要再脱啦!”幸亏小仙女儿喊得及时,要不然阿花就要当场脱得一丝不挂了。
……
长街上,陈玄丘安步当车,信步游走,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走得极慢。
他的小师弟无名还有众多随从仪仗散乱地走在大街上,看见个像是好事的行人,就热情地拉住人家,讲述方才发生在奉常寺的雷击事件。
方才九道殷雷,大晴天的炸响,整个中京尽皆听得清楚,大家对这“旱天雷”本就充满了好奇与猜测,如今这些人一讲,那算是“官方公告”了,极具权威性,大家自然喜闻乐见。
尤其这“官方公告”比他们自已努力发挥那可怜的想象力做出的猜测还要离奇,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恶趣味,所以好事者听完了马上就会很热情地加入“传谣”的行列。
陈玄丘停在一个包子铺前,装模作样地正想问问价钱,一个布衣荆裙的少女从巷子里钻了出来。
布衣少女从一户人家低矮的窝棚上揪下一根稻草,往自已头发上一插,就一头扑上前去,一把抱住陈玄丘的大腿,哀嚎道:“好心的大老爷,求你买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