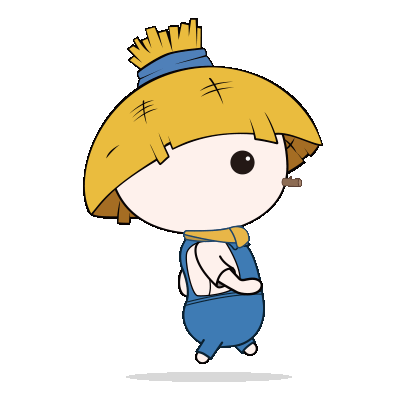操劳一晚,床上娇俏玲珑的小人沉沉睡去,一身羊脂玉般温软细腻的肌肤,已经满是暧昧的烙印。
贺承奕耳根发烫,为她掖好被子,遮住那些让他蠢蠢欲动、不知餍足的痕迹。
只露出一张欺霜赛雪的小脸,脸颊还带着未褪去的靡艳潮红,唇瓣红肿饱满,惹人怜惜。
即便再想与她温存,贺承奕也知道,天亮了,他不宜久留。
他俯身吻了吻女子的眉心,穿戴整齐,简单将杂乱的屋子收拾一番,纵身从窗户离开。
乔十一早已等候多时。
然而,看见贺承奕的身影从卧房出来时,他却犹豫了。
影卫队固然是帝王亲信耳目,但心中也不是全无家国大义。
镇北王一门赤胆忠心,贺世子自幼在沙场长大,杀敌无数,战功赫赫,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
他今天便是打赢了,将贺世子的项上人头给陛下提去,除了给陛下解气,也于事无补。
况且……昨日听长公主所言,她已失身于陛下,此事上不上报似乎并无影响。
思及此,乔十一隐回暗处,目送长公主的奸夫离去。
另一边,顾彦辰自诩天纵奇才,却在个小毛贼身上栽了跟头,回到明雅轩时满身火气,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
抬脚走进屋里,却不慎踩到一片碎瓷杯,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摔个狗吃屎。
定睛一看,他屋里那些古董字画全被砸得稀碎,地上一片狼藉,比遭过贼还混乱。
顾彦辰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沉声把小厮叫进来问缘由。
那小厮收了吕嬷嬷的好处,自然是添油加醋。
苏妤只是哭闹砸东西,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辱骂诅咒将军和少夫人,说得那叫一个声情并茂,叫顾彦辰怒火滔天。
他大步走进内室,见苏妤大剌剌在他床上睡得正香,一把抓住头发将人提了起来。
苏妤正梦到自己干掉长公主,正式成为将军府当家主母。
还没来得及庆祝,就感到头皮一阵钝痛,霎时眼泪狂飙,怨怼地瞪顾彦辰。
“混蛋!不是喜欢你那什么公主吗?有本事去了别回来啊!”
苏妤心中还堵着气,瞧见顾彦辰满头大汗,更觉得他是在长公主那边搞舒服了才肯回来。
“这是本将军的院子,本将军想回来便回来,轮得到你置喙?”
顾彦辰被气笑了,他倒是不想回来,可乔楚那边压根不让他进门。
想到乔楚,他心中泛起几分意动,未纾解的欲火又噌噌冒了起来。
他看了眼床上衣衫半解的苏妤,把到嘴边的斥责咽了下去,只是语气依旧透着说教的意味。
“住在府中,有什么不满可与我说,何必动手砸东西?那些个摆件字画可都不便宜,寻常人万金难求。”
苏妤气鼓鼓地捶他胸口,“说到底,你还是嫌我出身不好,不比长公主有钱有权给你长脸,臭男人德行!”
顾彦辰心里倒真是这么想的,只是他现在急着做些亲密事,不好说出来破坏气氛,便温声哄着苏妤。
“乔楚毕竟是长公主,我去一趟,只是给她个面子,应付母亲和悠悠众口,实则并未和她圆房。”
“本将军知你心眼小,放心,宝贝都给你留着。”
在军营时,顾彦辰和苏妤聊的话题便十分出格,只是她一直吊着顾彦辰,不曾真正与他亲密。
如今有陛下赐婚,他自是不必委屈自己。
夜深人静,被折腾得快散架的身子,哪里都疼,撕裂般的痛楚,火辣辣的让她睡不着觉。
她本以为陛下赐婚是个美好的开始。
她会风风光光嫁给顾彦辰,度过一个舒适而满足的洞房花烛夜,生下长子,一步步斗倒长公主……
她本以为和顾彦辰这般威猛俊逸的将军在一起会很快活。
可是没有!
他回来后没有沐浴,一身粘腻熏人的臭汗。
他是习武之人,手劲大,也丝毫不怜惜她青涩稚嫩,只顾他自己。
更没有温存和照顾,倒头就睡,把她像个破布娃娃一般丢在旁边。
苏妤暗暗咬牙,在这一刻,对顾彦辰的恨意达到了顶峰。
凭什么?凭什么要了她又不珍惜?!总有一天,她要让顾彦辰悔不当初,她要把他狠狠踩在脚下!
因为相同的原因,乔楚和苏妤第二天都没能起床,一觉睡到晌午才幽幽转醒。
不同的是一个面色红润,眉眼动人,处处透着被男人滋润的妩媚,而另一个如雨打娇花,被摧残得不成样子。
流苏进屋服侍乔楚更衣洗漱,看见那一身雪腻肌肤上的吻痕和指印,吓得失声,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殿下,您……”
乔楚慵懒地打了个哈欠,眼角眉梢都透着春意,显然被某人伺候得很舒服,“怎么,有事?”
流苏结结巴巴道:“将军昨夜回明雅轩了,听说一晚上动静没歇过,您……您……”
她想问的是,将军不在,殿下身上的痕迹是谁弄的,却又没那个胆子。
乔楚却误会了她的意思,大方承认,“放心,你家殿下睡的男人,比顾彦辰只强不弱。”
心脏脆弱的流苏差点当场晕厥。
房顶上,乔十一也是满头黑线,长公主真乃大昭第一奇女子,对房事也这般直言不讳,难怪连陛下都栽了。
翠兰苑,顾夫人用着午膳,幽幽开口,“吕嬷嬷,什么时辰了?”
吕嬷嬷恭敬道:“夫人,刚好午时三刻,明雅轩那位,这会子还没起呢,听说,昨夜少爷被她缠了一宿。”
顾夫人柳眉微蹙,脸色阴沉,“难不成真是个狐媚子?这般不知廉耻,传出去将军府的颜面都要被她丢尽了!”
“吕嬷嬷,找几个丫鬟婆子过去,让她搬到杏花阁住,再好生教导规矩,去去狐骚味。”
吕嬷嬷眼里闪过精光,“是,奴婢定会时刻督促,必不让苏姨娘扰了少爷勤学苦练。”
顾夫人喝了一盏茶,想起什么,又问,“长公主殿下那边呢?听说辰儿昨晚去过,可有什么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