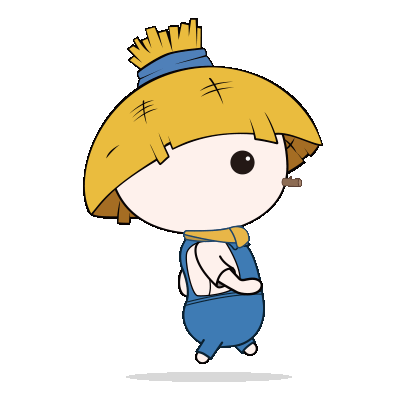江梨脑子嗡嗡响,穿越前她才二十三岁,就让她无痛当妈?
“你要是愿意,他明天就来咱们村相看。”
“小兰,还是算了。”
江梨拒绝的原因不是富贵不能淫,而是她有洁癖。
这庄国梁以后是要天天去养猪场的,她一想到就吃不下饭。
见江梨拒绝,李春兰也叹了口气,点点头道,“你不愿意也正常,换我我也不愿意做后妈。”
“只是梨子,能出得起二百块彩礼的人家太少了,这一来二去的,不就把你的青春耽误了?”
“小兰,谢谢你,还仔细替我想着这些。这些年要不是你和婶子偷偷接济我,我这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江梨充满感激地握着春兰的手,李春兰捏了一把江梨的脸蛋,嗔怪道,“你说什么呢!以前淑珍婶子对我多好。
再说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在我心里,你就跟我亲妹子没两样。”
江家愁云密布,没人顾得上江梨。
她走回柴房反锁门,掏出怀里的包子小口咬着,柴房稀疏的房顶露出几颗星子,月色皎洁。
江家是不能呆了,这年头,没有工作的只能下地挣工分,不然就得喝西北风。
农活她是干不了一点,难道真得靠嫁人改变处境?
不!
就算要嫁,也不能是庄国梁。
庄家的情况太复杂了,庄国梁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姐姐已经出嫁,三个哥哥也各自娶了媳妇,每家至少两个娃。
庄国梁的老娘是个寡妇,泼辣能干,在家里说一不二。
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没分家住在一起,隔三差五就有矛盾。
这样的人家江梨不想掺和,不能嫁,也不敢嫁。还是想办法找工作靠谱些。
这么琢磨着,江梨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早上被一阵喧闹声吵醒。
她没理会,翻身打算继续睡,却没想到吵闹声越来越大,江梨摸着饥肠辘辘的肚子爬起来,开门进了厨房。
奇怪,往日天没亮江家全家就下地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江梨没管这些,从鸡窝里摸出两个还热乎的鸡蛋煮熟吃了。
东屋里传出王菊花压抑的哭声,“你这死丫头怎么这么心狠呐,你死了让妈怎么活?不嫁了,不嫁了还不行吗?”
床铺上躺着的江红梅脸色惨白,脖子上一道淤青深得吓人。她开口,嗓音破碎,“妈,让江梨去嫁。”
一旁的周老太怒了,“你闭嘴,这么好的亲事能轮上她?”
王菊花抹着泪,“是啊,红梅,你不想嫁齐少强那咱们就不嫁。再相亲就行了,这江梨凭啥嫁过去享福?”
江昌义抽着旱烟一直没说话,一开口却是石破天惊,“让江梨嫁!”
“当家的!”
“昌义!”
“这亲事与其便宜了别人,不如让给江梨。怎么说我们也是她亲奶亲大伯,她爸妈死后,我们养了她那么多年。
她以后享了福不帮衬我们,全村人都会戳她的脊梁骨。”
“况且江梨那丫头性子软和不记仇,总是会念着骨肉亲情的。
再说了,江家是她娘家。她一个乡下丫头嫁进城里,以后还得靠娘家撑腰,她敢对咱们不好吗?”
这话说得有理,王菊花和周老太都忍不住点头。
周老太心中暗恨,“那彩礼不能给少了,至少要三百块。”
她大孙子天赐还在读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拿了彩礼钱,也好给他好好补补。
“好了,下地去!”江昌义把王菊花拉走,“都戳在这里不上工,年底喝西北风啊!”
王菊花有些担心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女儿,“红梅,你听见了,你爹答应了,你可别再做傻事了。”
江梨一边啃着李子一边偷听,等几人出来,她已经躲进了柴房里。
只听见院子里王菊花尖叫一声,“天杀的,哪个丧良心的不要脸,把我们家的李子都给偷光了!”
王菊花在院里破口大骂,她家李子树是十多年的老树了,结出的李子又大又甜。
好不容易快熟了,她这些天一眼不错地盯着,就怕村里的小孩偷吃了。
没想到就今天一眼没顾上看,就被人偷了。
“是不是江梨那死丫头吃的?”周老太举起拐杖就要去算账,那李子是留给她大孙子的,这死丫头臭不要脸,她也配吃?
江昌义拉住了周老太,“妈,江梨的胆子你还不知道吗?她不敢偷吃。”
然后又压低了声音呵斥王菊花,“闭嘴,就算是她吃的,这些天也不许打她。”
要嫁人了,得念着江家人的好。
江昌义来到柴房前拍门,“梨子啊,我和你大伯娘下地去了,你病好些了吗?有什么想吃的就让你阿奶做。”
江梨听着江昌义的声音打开了房门,咳嗽连连,一张消瘦的小脸苍白不已,“大伯,我还是头昏脑胀的,可能是昨天上山累着了。
我下山的时候晕倒了,大队的赤脚大夫说我营养不良,得好好补补。”
江昌义和蔼的面孔一瞬间流露出不悦,很快又强压了下去,他挤出个笑容,“那,那就让你奶杀鸡,给你好好补补。”
周老太开口就要骂,被江昌义一个眼神制止,江昌义背着双手,“双抢这些天大伙也累了,杀了鸡都能沾点油水。
妈,你今天就别下地了,红梅和梨子都病了,你就在家做饭。”
周老太平时虽然厉害,可儿子拿定了主意,她也不敢反驳。
她骂骂咧咧地洗衣裳,挑水,打猪草,杀鸡做饭。
这些活路平时都是江梨上完工回来干的。周氏她好些年没干过了,今天一口气做了,把她累得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