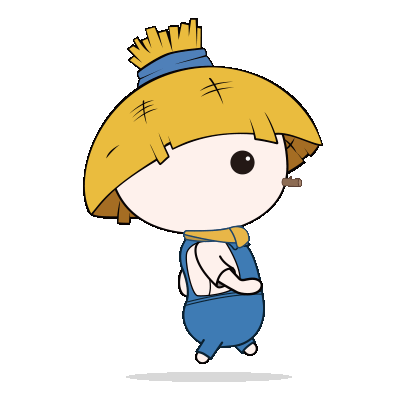她以为是风吹动了窗户,可转念一想不对,江家在村中央,前后都是严严实实的屋子遮挡,哪来的风。
江梨翻身起床,顺手抓起撑门的棍子,心扑通扑通狂跳,屏住呼吸,躲在了床脚。
果然,在听见屋里没动静后,窗户慢慢打开,一个黑影蹬上了窗台。
咚地在窗户边落下,然后又摸黑到了床边,手往隆起的被子里伸过去。
江梨大喝一声,手里的木棍毫不留情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二赖子只觉得后颈剧痛,还没来得及叫喊出声,人就扑通一声倒地。
等人在地上一点也不动弹了,江梨摸了自己的额头一把,满是冷汗。
点亮屋里的烛火,赫然露出一张熟悉的脸,秃头黄皮,眯缝小眼睛,跟个虾米似的蜷缩在地上,鼻青脸肿的,正是白天见过的二赖子。
一个大男人半夜摸到姑娘屋里,想要干什么不言而喻。
只是偷东西还算是轻的,怕就怕的是,有人盯上了江梨的人,还有江梨妈妈留下来的东西。想连人带财产一并吞了。
江梨的冷汗一直没停,是她大意了。
村里家家户户离得近,东家放屁西家都能闻到。
她拿了抚恤金,大队长还给了她记分员的工作,父母双亡,又和大伯一家关系不好。
在村里人看来,她简直就是个掉在路边的香饽饽,谁都能来啃一口。
先是郭海峰,后是二赖子。
像这样打主意的人,还有多少?
要不是她幸运地惊醒,又恰好有着神力,那她是不是就得嫁给二赖子这种人了?
江梨又气又恨,咬着嘴唇,找了草绳把他的手脚捆住,又摸黑到厨房拿了菜刀。
她憋着一口气把二赖子身上的破衣裳割成布条,用大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两个膝盖处。
然后就是拖死狗一样把人拖到村口的粪坑,二赖子中途醒过来了一次,只敢低声求饶,又被江梨一拳打昏。
咚的一声,二赖子被她抛进了粪坑,咕嘟嘟咕嘟嘟,饱饱地喝了几口。
江梨摸黑回了屋,出了这样的事情,她没敢睡觉,睁眼到了天明。
天色麻麻亮的时候,村口的茅坑传来一声划破天际的尖叫,“抓流氓啊!”
“臭不要脸的东西,敢蹲在茅坑里偷看大姑娘上厕所,也不看看老娘我是谁!”
说话的是村里屠户家的媳妇,人称张三娘的母老虎。
她刚嫁来大树坡的时候,在后山的水潭洗澡,有不长眼的几个半大小子偷看,被张三娘一手一个按住浸在水潭里涮菜,淹得直翻白眼。
这还不算完,又拽住混蛋小子的脚脖子,倒提着拖回村找他们家老娘算账。
带着她人高马大的男人坐在人家门前整整骂了三天,直到每家赔了她一块钱才算完!
张三娘拿起舀粪的粪勺就打,一下一下精准砸在二赖子的头上。
被淹了一夜不成人形的二赖子,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边捏着鼻子围观的大娘们厕所也不上了,给张三娘助威,“打他,不要脸的小流氓。”
“这人是盲流子吧,看着不像我们村的。”
“来个男人把他捞起来瞅瞅!”
“真恶心,谁愿意去谁去,我可不去。”
有人扔了根麻绳到粪坑里,另一头绑在树上,二赖子使出吃奶的劲拉住爬了上来。
“怎么看着像二赖子啊?”有人认出了二赖子那标志性的凸嘴大板牙。
“去找他娘过来认认!”
二赖子的娘抹着眼泪跑来,发现自己孩子奄奄一息,话都说不出来了,“天杀的,谁把我家二赖子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
张三娘把粪勺往地上一杵,“我打的,咋了?”
“他藏在茅坑里偷看,我没戳瞎他的狗眼算不错了。你就是告到大队长那,也是我占理。”
“妈,我没偷看!”
二赖子哆哆嗦嗦,一张口喷出不明的黄白物体。
围观人群齐齐退了一步,有那些个爱干净的小媳妇,当场吐了出来。
“没偷看你一大早蹲在女人的茅坑干什么?”张三娘横眉怒目,恨不得生吃了二赖子。
“我,是有人故意把我打晕了扔在这的。”
“谁打的你?人家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我看你就是撒谎!一大把年纪娶不上媳妇,就在这偷看女人屁股。”
“谁看了我媳妇屁股?我要他的命!”
牛屠夫握着杀猪刀杀气十足地来了,二赖子下意识缩了下脖子,往他妈身后爬了两下。
“大队长来了!”
“一大早又在这闹什么?”
“二赖子,你又犯什么错误了?”江保山烦不胜烦,又是这个二赖子,老光棍一条,整天在村里招猫逗狗调戏小媳妇。
“你这是严重的耍流氓罪,死性不改,我看你就该下农场改造!”
“大队长,可不能啊,我就二赖子这一根独苗,他要是下农场我也不活了啊!”二赖子娘哭得肝肠寸断。
“大队长,我保证他以后会老老实实的,再也不敢了,大队长……”二赖子娘给跪下了,头磕得砰砰作响。
“张三娘,你们怎么说?”
张三娘看了一眼红着眼的二赖子娘,这一个村里的,要是断了人的根,保不齐二赖子娘能干出什么癫事来。
好在她刚解开裤腰带就发现了二赖子,没让人看光,算了,就当她自认倒霉吧。
“大队长,我都听你的。”
江保山松了口气,他也不想弄出个下农场改造的小混混来,坏了生产队的名声。
张三娘大度又懂事,他也不能让老实人受委屈。
“二赖子,你赔偿人家张三娘一块钱,给队上挖一冬天沟渠,粮食自带,没有工分。
明年开春,你挑粪给村里后山的果树上肥料。”
挖沟渠,上粪都是又苦又累的活路,谁去了都得脱一层皮,二赖子这回有苦头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