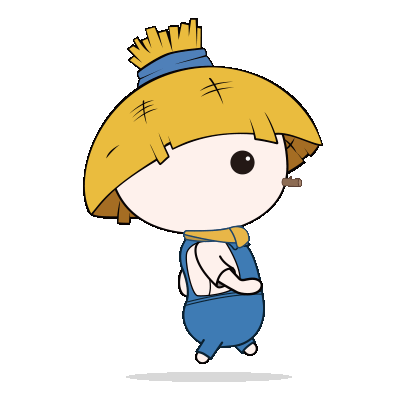且惠是一路小跑着下楼的, 像一只误闯禁区受了惊吓的小兔,急于逃离雄狮的领地。
刚才上楼时,门只不过虚掩了一下, 没有完全阖上。
她跑进去,用力地甩在身后,脱力般地背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且惠抚着胸口,试图安抚那颗砰砰直跳的心, 它太快太急了,像随时都会从喉咙里蹦出来。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酸枝木多宝格里那座自鸣钟,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
月光在窗前撒下一片暗影, 她盯着看了许久,气息才渐渐地平和了下来。
且惠坐到书桌前,拿起笔重新看了眼卷子,继续往下做选择题。
“张某基于杀害刘某的意思将其勒昏, 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为毁灭证据将刘某扔下悬崖,事后查明, 刘某不是被勒死而是从悬崖坠落致死,关于本案, 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她扫了一眼答案选项,勾了D,张某构成故意杀人既遂。
但翻过一页,答案还多选了一个A, 张某在本案中存在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
她敲了敲脑袋,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摆在第一个, 怎么就没有勾上?
行为人误以为第一种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实际上危害结果是由第二个行为造成的,这是典型的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啊,老师讲过好多遍了。
且惠订正的时候,笔尖忽然在字里行间顿住。
她心浮气躁地用笔刺了刺书,厚厚的纸张上,戳出几个不规则的小黑点。
越想越觉得不公平,他的反应怎么就能那么平淡!那么正常地叫她回去休息。
且惠扯过镜子照了照,黑色长发下一张干净清丽的素颜,明明很好看。
很快她懂了,人家沈总见过的佳丽太多,自己根本不算什么。
她忿忿地把镜架倒扣在桌上,关上书去睡觉。
到睡前,薄薄的被子盖在她身上时,又稀里糊涂地笑出声来。
且惠觉得她矛盾幼稚,这有什么值得计较的?
沈宗良始终维持着绅士风度,手规规矩矩地放着,没有一时片刻的逾矩还不好?
足以证明他是正人君子,处变不惊,八风不动,是个性情十分平稳的男人。
那她是在气什么?气他没做一些登徒子行径?还是气他的视自己如无物。
难不成她是希望他会怎么样吗?还是她先对他有了别样的心思?
天,她居然会有这样的念头,这太可怕了。
胜负欲也不该用在这么奇怪的点上。
且惠疯狂地摇了摇头,她不能为这种事分心。
如今这样的境遇下,又哪里来分心的余地呢?何况对方还是沈宗良。
她就这么昏沉地睡过去,胡思乱想了一整个晚上。
以至于那一天到最后,留给她的印象就只剩一点模糊而朦胧的概念,那就是,沈宗良身上清冽安定的气息令她毫无反抗之力。
倘若他不是这么磊落,倘若他再私心私欲一点,她即刻便要束手就擒。
从那一晚以后,且惠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她在刻意拖长战线。
且惠常在图书馆泡到深夜,隔着一张白色的挡板,对面的人就没看过她抬头,只有间断的翻书声。
就连周末这样的日子,辅导完参加演出的小朋友们,且惠也会再回学校去。
图书馆里找不到位置了,她就去自习教室,学到熄灯赶人才肯走。
沈宗良手头上事多,但每天日落之前,是雷打不动要回家的,得烧上一炷晚香。
但次次都不见钟且惠,她那扇菱花窗像永远关上了一样,只剩庭前满架的蔷薇。
有时候深夜回来,也看不到她房里的灯光,四处是灰蒙蒙的寂静。
连黄秘书都问:“钟小姐这么晚了还在外头?”
沈宗良沉着脸没应这句,只吩咐他早点下班回去。
女孩儿家的心思海水一样深,捞也捞不到,谁知道是哪里逆了她的骨头了。
又一个周六下午,且惠对着一群小女孩,十分严格地纠正舞姿,一点偏差都不许有。
她多次跟她们强调,这是登台演出,稍微一点点的不整齐,都会被无限放大。
否则怎么说台下十年功呢?观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要禁得起检验不容易。
不光孩子们辛苦,且惠也心力交瘁,她反反复复地做规范演示,不厌其烦地教她们。
一个简单的动作,有时候甚至要做上十来遍,才能达到她预期的效果。
有女孩累得受不住,坐在教室的地面上,瘪着小嘴说:“早知道不报名了。”
且惠听了,蹲下去给她揉腿,她手法和力道都合适,小女孩冲她笑了笑。
她看了一圈旁边的人,“但是你们想啊,学了这么久芭蕾,有一天出现在电视直播的晚会里,被你的亲人还有老师同学们看见,心里是不是很骄傲?”
说出这些话来,且惠也隐隐为自己脸红,不知不觉中,她也成了哄小孩的大人。
但小姑娘们都大声地笑着喊:“是!”
且惠点头,拍了拍掌:“好,休息十分钟,我们再练最后一次,就可以回家了。”
“耶!”
这堂课上到将近七点,家长们早就在门外等着了,也都知道是为了晚会集训,因此并无什么牢骚,反而钟老师长、钟老师短的,钟老师辛苦了。
且惠送走学生们,她也回到淋浴间,换下舞服,快速冲了一个澡。
她换上自己的衣服出来,在物品柜前收拾东西时,看见教室忽然停电的通知,今晚只能回大院里去了。
出了地铁口,且惠抄近路蹿进一道胡同,没多久就看见大院的门。
看见路边大而红的糖葫芦,上面裹着一层晶莹微黄的糖浆,还特地停下来买了一串。
且惠走进大院时,正赶上广场舞的时间,中心花坛那片空地上,站满了大爷大妈。
她路过,冲几个眼熟的奶奶弯腰点头,笑了一下。
刚要转头,就看见沈宗良离她只剩几步之遥。
他穿着西装,脖间的领带系得十分饱满,擦着树梢上的白花瓣走来,文质彬彬的模样。
应该是赶回来给他爸爸烧香的,这是沈总每天傍晚必做的功课。
躲是躲不过去了,钟且惠只能生硬地问好,“沈总。”
这么多天不见,她好像又活回去了。
且惠表现得仍像最开始时一样,几乎被他无从收敛的气场吓到。
她背着双肩包,大拇指卷吊住一根袋子,手上举了根糖葫芦,因为紧张而瞪大了眼睛,活脱一个中学生。
沈宗良倒不见异样,照常寒暄,“回来了。”
她点头,脚趾头不安地拱动,“嗯,今天学校停电,早点回家。”
沈宗良冷淡地嗯一声,“日日不见你人,还以为你不住这里了。”
他的声音始终沉稳,不含任何一丝多余的情绪,令她想起高中班主任训话。
且惠清凌凌地笑了一下,“是有这个打算的,我迟早都要搬走。”
他掸了掸肩上沾着的花瓣,“当然,你我都是要走的,谁还在这长住么?”
没想到被他客观也无情地顶了这么一句回来。
且惠低垂着的一张莹润小脸,一瞬间青白交错,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要换了旁人或许还好些,偏偏沈宗良是个最会听信听音的,她还惹不起。
二人正僵持着,袁奶奶过来叫她,“且惠,你会不会跳《沂蒙颂》?我们正排练呢。”
这段日子下来,她对且惠的情况大致了解,也知道她在教孩子们跳舞。
且惠懵了几秒,举着糖葫芦不知所措,她说:“会倒是会,但我今天有别的......”
袁奶奶急吼吼地扯过她,“会就行了,你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转圈是这样吗?”
或许她们真的着急解决这问题,且惠想,反正示范一遍也不要很长时间。
她看了一眼旁边的音响和演出服,问:“奶奶,你们是要去比赛吗?”
“对呀,请的老师还要明天才能来,你先给我们示范一遍好了。”
且惠哦了一声,她脱下双肩包来,不知道往哪儿放。
因为心里存了份惧怕,连左顾右盼找地方时都避着沈宗良,不敢去触他的霉头。
但对面已经伸出一只手,指骨分明而白净,握住了包上的两根肩带。
沈宗良用下巴点了点不远处,“去跳,我帮你拿着。”
才惹他不高兴,且惠哪里还敢有半个不字,她索性把糖葫芦也给了他。
她小声说:“辛苦你,我很快就好。”
很意外,沈宗良的脸色竟柔和下来,他说:“没事。”
且惠边走边把头发缠起来,扯了扯身上的一字肩短T,“各位奶奶,我给大家跳一遍,水平也不是很高,勉强看一看,多见谅吧。”
她声音轻柔,俏皮话也说得好听,逗得长辈们都笑了。
音乐响起来,且惠踩着节拍优美摇动手臂,轻盈,灵动,纤软的腰肢如风中的垂柳。
她踩着小碎步,高抬着手往前那一下,冷不丁打在杏树垂下的枝条上,扑簌簌落了一阵花雨。
且惠专注着跳舞没在意,倒是远观的沈宗良心颤了一下,仿佛被花淋到的人是他。
他想到她刚才低眉顺目说辛苦你的样子,怯生生的。
沈宗良破天荒地反思起来,他的语气是否太凶了一点?
她回不回家,在这里住多久,几时候搬走,都是她的自由。
他有什么资格为这些细枝末节动气?未免太霸道。
再说了,他动的究竟是哪门子气!就因为十来天没见她,一见面话讲得就不好听?
细究起来,钟且惠好像也没说什么,她无非陈述了一遍事实。
他正盯着且惠出神,肩膀忽地被谁重重拍了一下,是寻过来的唐纳言。
唐公子出口抱怨,“在门口等你半小时了,您老人家是左也不出来,右也不出来。我还当您给人扣下了呢,合着是在看姑娘跳舞啊?”
沈宗良狂妄不羁的语气,“怎么,这世上还有人敢扣我呢?”
唐纳言眯了眯眼,定睛一看,“唷嗬,这不且惠吗?”
“是她。”身边人出声肯定。
沈宗良举着糖葫芦,姿势看上去蹩脚拧巴极了,像橱窗里穿错时装的模特。
目光逡逡巡巡,唐纳言欣赏了一番他这造型,权当个新鲜事儿看。
他明知故问:“这包儿,这糖果子,也是她的东西?”
沈宗良给了他一个白眼,“那还能是我的?”
唐纳言笑:“推倒油瓶都不扶的沈总,居然给姑娘拎起包来了,好好好。”
他漫不经心地解释,“事赶事到了这地步,不为别的。”
“对,就你和她的事特别多,咱小庄来了都要靠边。”
沈宗良没回嘴,眉目却舒展了几分,勾唇笑了下。
且惠不敢叫他久等,跳完后,认真指点了一下奶奶们,就飞快过来。
半壁斜阳里,沈宗良的身形笔挺而优越,站在郁郁葱葱的古槐底下,落满一身斑驳晃动的树影。
每一次撞见他,且惠都能浅显直观地感受到,沈宗良就是那一类,永远站在被爱的上风口的人。
可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免俗,不要钻进华而不实的套子里。
他的家世过分高了,爱上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她全都知道,全都明白。
但她也知道,明白归明白,世上的事并非明白就能完全做到,这是两码事。
见唐纳言也在,且惠喘吁吁地问了个好,“纳言哥哥来了。”
然后略带歉疚的,主动从沈宗良手里接过她的东西。
唐纳言素性温和的,笑着点了点头,“且惠,最近还好吗?”
“挺不错的。”
且惠说着,看沈宗良捋开了肩带,她会意地转了一个身,由着他挂在她肩上。
而后听见他父亲式的口吻,“这里头放了多少本书?怎么那么重!你天天就这么受罪呢?”
语气里,是连无心之人都能感受到的亲近,不同寻常。
弄得且惠有些羞赧地望了一眼唐纳言。希望他不要误会。
她轻声:“不是的,因为要写一篇小论文,明天我放下两本好了。”
沈宗良指了下她的手,“刚才打到树枝那一下,检查看看。”
且惠抬起手腕,白皙的手背上果真有道红色划痕,只是不太深。
她低头瞧了一眼,说:“不要紧,回家洗洗就好了。”
沈宗良叮嘱道:“那也不要掉以轻心,擦点药。”
“嗯,我晓得了。”
下一秒,唐纳言清了清嗓子,当了个不解风情的角儿,打破这份暧昧流动。
他附到沈宗良耳边说:“您再舍不下,有话也回来说成吗?今儿这局可迟不得。”
“别急,”沈宗良伸手拧了下领带,“天塌不下来。”
且惠看着两人走远,他们的对话她没能全听清,唯独装进了那一句舍不下。
舍不下什么?沈宗良有什么可舍不下的?是她吗?
讲什么地狱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