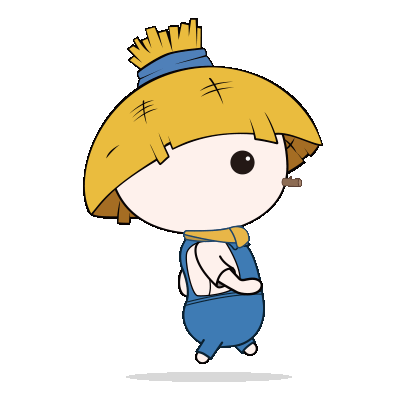魏晋丰憋住笑, 朝他家谦明送了个眼风。
他往庄新华那儿坐了两步,“打进门我就觉得您不大对,今儿受什么刺激了?”
庄新华龇着嘴:“还不就是去找且惠, 在那个了不起的大院里,我睁眼看着她跑上了楼!”
雷谦明问:“跑上楼?她跑上楼你就受不了了,楼上谁啊!”
“就是棠因她小叔叔。”魏晋丰回头跟他解释。
那头哦了好长一声,咋呼道:“怎么,他俩都住在一起了?”
庄新华又朝他撒火儿, “幼圆把她外公的房子给且惠住了,这都是多早的事儿了!你就好像不跟我们一个世界似的。”
雷谦明不懂,“沈叔叔是当孝子去的,这全京城都知道, 钟且惠是去干什么的?”
说完,和魏晋丰互换一个眼神,别有深意地笑了。
“看看你们,一肚子的鸡鸣狗盗, ”庄新华点了根烟说:“且惠的房子在装修,她没地儿住了。”
雷谦明笑,“原来这么回事儿, 我还当她有什么目的,是我小人之心了。你也怪不着我, 太多小女孩子费劲往咱们小叔叔身边靠了,谁让他那么招人来着。不过,我说庄儿,你要是喜欢她, 早点表白得了。正正好,你不刚和晓乐闹掰吗?”
魏晋丰歪过头吐了口烟, “我的天,又分手了,谈一个散一个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雷谦明说:“这不明摆着的吗?心里惦记钟且惠啊,看谁都不是那意思。”
“别扯那些没影儿的。”庄新华烦闷地摇了摇手,“你们不知道,我跟她表白没有用,她会笑死,然后叫我少发点癫。没办法,我们俩实在是太熟了,她甚至看过我穿开裆裤,我真张不开这嘴。”
雷谦明不以为然地切一声,“这他妈也能算个事儿?钟且惠还和我一张床上打过滚呢!你还别这么看着我,小时候我和她是邻居。但那又怎么样,我要喜欢她照样能使手腕子。”
“就......只能眼看着她跟了沈二呗。”魏晋丰摊了下手。
刚说完,雷谦明就轻轻搡了他一下,示意他别火上浇油。
魏晋丰反而喊上了,“那本来就是!让他去追又不敢,不就只剩这么个结果了,还能怎么样。”
庄新华闷着头抽了两口,“晋丰,换了你会怎么办?”
魏晋丰想都没想,吸了口烟说:“我可不管这么多,只要我起了念头,管这瓜甜不甜的,先摘下来吃了再说。”
庄新华撇他一眼,上下打量了小魏一溜够,忽然冒出一句,“你他妈什么星座的?”
“我个人没素质,和星座血型有什么关系啊!真能扯。”
“......”
雷谦明觉得他单纯口嗨,“你那么喜欢棠因,也没见你敢放一个屁啊?”
“棠因是什么人哪!”魏晋丰说:“我敢胡来一下,她爹能把我脑袋揪下来。”
庄新华想象了一下他被沈元良训斥的情形。
他低声笑出来,“也是。”
雷谦明揽过他的肩膀,“你要是想把她约去阿那亚,兄弟可以帮你。但之后她能不能答应,可就全看你自个儿的了。”
“成!”庄新华想了会儿,拿定了主意,“行与不行的,我总要试这么一次。”
魏晋丰也在旁边鼓动他,“对嘛,打起精神来,咱别的不如沈二,追女生总可以压过他,毕竟年轻十岁呢。再者说了,你和且惠认识的时间比他长多了,根本不是一个体量的。你看那天你喝多了,我一打电话人就过来了,她心里是在乎你的。”
烟雾缭绕里,庄新华迟疑地点了个头。
但他心里隐约有种感觉,这件事情成不了。
且惠的性子他了解,她对身边人都很好,不只是对他。
不管是他有事情,还是幼圆需要帮忙,她都会赶过来的。
但这是他珍藏心底的初恋。
是他在审美机制还未健全的时候,迎头撞上的最强烈、最真实的吸引。
他总是记得那个浑身湿透了,自己都没剩了两口气,还拼命托他上岸的小且惠。
庄新华夹着支烟,飘飘渺渺地想起他们的重逢。
两年前,且惠来京市上大学,他去机场接她,路上堵车到晚了二十分钟。
她就乖乖地站在那儿等,一步都没动,看他来了,挥着帽子喊庄庄,我在这儿。
而他几乎不敢认,面前的女孩大眼碌碌,五官浓丽得让人心惊。
那个时候他就在想,可一定不能让别人把她追去了啊。
可且惠的态度那么明显,多少次都把他的试探给堵了回来,笑话他是在犯傻。
他也只好装作那些都是拙劣的玩笑,尽量演得逼真。
既然她没开窍,现阶段还只知道闷头读书,那他也可以等。
但半路怎么会冒出个沈宗良的?真他妈伤脑筋。
出了鬼了,沈家老二日常一副傲慢冷淡的样子,怎么就对且惠不同?
且惠也是有点怪的,和别人相处总是不远不近的态度,居然肯去体贴沈宗良。
他们也不过就认识了月余,能有多少根深叶茂的情分在?
这么分析了一遭,庄新华掐了烟,站起来,大步往外走。
“酒还没喝完呢,你就这么回去了!”魏晋丰喊。
他朝后面摆摆手,“不喝了,我先睡上一觉,再找你们商量。”
三十号那天,且惠下午没课,做了几套题,傍晚到的电视台。
今夜是小朋友登台演出的日子,总归要她这个当老师的在场的。
化妆间里乱糟糟,一会儿梳子不见了,一会儿又要找发卡。
且惠跟着她们一通忙,最后从头到脚,给每个人检查了两遍,才满意点头。
她弯腰拍拍领舞的肩膀,“别紧张,你们已经排得非常好了,就和平时一样好好跳,没问题的。”
“知道了,钟老师。”
后台闷热,且惠脱了身上的短外套,挂在臂弯里。
孩子们候场时,她跟家长们一一打过招呼,走开了。
等表演结束,她们就要各自回家庆功,也不用上她这个老师了。
她的老板郑晓娟正抓紧交际,和副台长有说有笑。她们是老同学。
且惠笑着过去,说她晚上还有事,先过去。
原本今天晚上,她就是不必过来的,但且惠在家坐不住。
总要亲眼看看学生们,鼓励上两句才好放心。
郑老师点头说好,“且惠,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国庆好好休息一下。”
“嗯。”且惠拨了一下头发,“国庆快乐。”
她礼貌地冲副台长致意,“再见。”
出了电梯走到大厅里,迎面一阵萧索的秋风,结结实实得冻人。
把穿着无袖针织衫的且惠给吹了回来。
她退回转角处,哆嗦着,小声嘀咕:“朗瑟特勒。”
有一只手从她肩膀上越过,给她递了一条深蓝色方巾,沾着檀木香。
身后一记温和关照,“又是汗,又是吹风的,当心着凉。”
且惠转头,笑了笑接下了,“沈总,你也在这里呀。”
她擦了擦眉弓处的汗,又觉得这样还给人家不大好,顺手收进了包里。
沈宗良收敛目光,看着她自然的动作,弯一弯唇角。
他说:“被押着来看晚会的,当个......无情的鼓掌机器。”
小年轻这类新潮的词,他说起来还是不大顺口,中间顿了一下。
上个星期,电视台的请柬发到集团,是行政处接的。
不巧,邵董带着几个老臣下基层了,临走前交代让沈宗良来镇场子。
还开玩笑说,要叫他这个东远的活招牌在全国都竖起来,不能只在资本圈里走红。
且惠穿上外套,指指上面,“可是都还没结束呢,就可以出来了?”
沈宗良扶着脖子转了转,“差不多得了吧,我坐到现在,已经腰酸背痛了。”
她打抱不平的语气,很强烈地抗议,“真是的,一点都不体恤上了年纪的人!”
“......”
沈宗良转脖子的动作僵在那儿,唇角无声抽动两下。
眼见得这小姑娘是越来越不怕他了,胆大得很。
他也是反骨头,竟隐隐有点得意。
毕竟他也从不缺她这一份毕恭毕敬。
且惠对他的迟愣浑然未觉。
她正经关怀他:“休息了两天,你的身体好一点了吗?”
“没怎么好全,还是只能喝点粥,”沈宗良索性自嘲上了,“我们老年人身体恢复得慢。”
这回轮到且惠失语,她很卖力地不让嘴角翘起来。
他们一起走出电视台,沈宗良摁了一下车钥匙,“送你回家?”
且惠心想正好省了自个儿打车。她甜滋滋地说:“那麻烦沈总了。”
面对她突然的转变,沈宗良见怪不怪地回:“您不用这么客气。”
且惠抿着笑坐上去,车里空气不流通,她又把外套脱下来。
她这件上衣很短,露了一截纤细腰肢在外面,昏灯暗影里,小姑娘的皮肤光滑白皙。
沈宗良开着车,视线避让着她这边,“七天长假,要回家看看妈妈吗?”
她摇头,眼睛盯着车窗外,“我接了个翻译的活儿,跟外交学院的两个学姐,就不回去了吧。”
今天上午彭学姐给她打电话,说有个参观团去阿那亚考察,缺几个翻译兼导游。
且惠答应了,一来彭学姐是她的老相熟,介绍过很多工作给她;二来幼圆他们也要过去,结束了还能度个假。
沈宗良想起了什么,“庄新华是不是也在外交学院?”
她现在坐他的车很放松了,放松到还能打下遮阳板来照一照脸。
且惠边检查妆容,抚平了鬓边的细发,“是啊,但他学国际关系。”
他点了下头,又问:“要去几天?”
“就三天吧,这种不会很累的。”且惠说。
沈宗良单手把着方向盘,“你翻译能行吗?不要误导国际友人啊。”
她立马就去翻包,把口译证掸开在他的面前,“不信你看哪。”
沈宗良端出长辈姿态,压着笑,“开着车呢,别闹。”
“咦?”且惠不满地收起来,“不是你先问我的?”
沈宗良淡淡一问:“这些证件你还随身带着?”
她打工人的自觉,“是啊,怕甲方同你一样怀疑,身上总是带着这些。”
小姑娘要强,他倒不怎么质疑且惠的能力,不过是和她逗咳嗽。
这么一说,沈宗良才掀了掀眼皮,“怎么,有人说过这种话吗?”
且惠云淡风轻的,说:“当然有了,好几次去商务会谈上当翻译,那些老板见了我就问,姑娘,你先说两句英文给我听听?”
她学得很像,老京片子客气又轻慢的口吻拿捏到位,还地道地吞了几个音。
沈宗良扯了扯唇角,“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总认为年轻漂亮的女性,专业功底就不过关。”
且惠嗤一声,“这个社会对女性一贯的偏见罢了。”
他沉默着,往旁边瞥了她一眼,说着自己还气上了,嘴唇微微撅着。
他们回了大院,一向清净的庭院里,呼啦啦站了一排人。
且惠疑惑地看了几眼,喃喃自语,“好像是万和的服务生?”
为首穿制服的那个,她在酒店大堂里见过两次,是那里的总负责,身上领着不低的职衔。
沈宗良停稳车,说:“是,我叫了餐。”
且惠觉得难以想象,“万和还能送餐啊?从来没听说过。”
像那种贵胄出入的园林,没了身份的加持,如今进去她都觉得拘谨,束手束脚不敢动。
即便是当年爷爷在,她也没见识过这样的阵仗和排场。
就是五岁那一年,在万和的荣宝斋过完生日后,且惠总记着那儿的鹅掌好吃。
央求了几回,爷爷才在一次开完会后,让后厨打包了一份。
但也只有那一次而已。
沈宗良倒很平常的样子,“不叫他们送,我总不见得还自己动手。”
“沈总,有一种东西叫外卖,你知道吧?”
他点头,“知道。但我吃不惯那些。”
“......”
对,您吃饭的碗都得镶金边儿。且惠腹诽。
他们走到台阶上,万和的大堂恭敬欠身,“沈先生。”
“麻烦你,送到楼上去。”沈宗良淡淡吩咐,又转头来问且惠,“你吃过了没有?”
她摇头,“没呢。光顾着我那群学生,就这么出门了。”
沈宗良细看她的脸,好像比刚搬来的时候,又尖了一点儿。
他沉默了一息,像责怪也像心疼,“你不能学我,总是不吃晚饭。”
且惠往上站了一个台阶,仍然仰望他。
她伸出食指在他面前晃了下,“我保证,今天最后一次。”
沈宗良笑了笑,“你最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