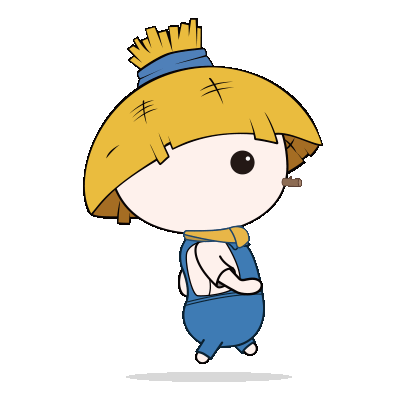好不容易挨到沈宗良面前, 且惠抬眼看他,夜里孤魂游荡一样的目光。
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沈宗良, 你怎么在这儿?”
沈宗良不动声色,借着月色端详她,“送了一位叔叔过来,等一等你。”
他是说了,且惠也没聋, 她听得很清。
她更不傻,明白沈宗良话里话外捎带手的人情,其实是特意为她而做。
试问还能有什么人需要他亲自送?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为什么非要来接她呢。
干嘛总是给她不容拒绝的照料?
她很怕。
怕这一份越来越明朗的心动, 会将自己引入歧途。
且惠捏着拳头,抬头对上他漆黑的眼眸,“就是说啊,你为什么要在这儿等我?”
她微卷的长发披在肩后, 一张素白的脸浴在月光里,耳尖上缀着圆润的珍珠。
那对珠子品相不错,光泽感极佳, 却仍比不过她雪白的脸。
沈宗良看着她这副较真的模样,一时想笑。
他眼中聚起稀薄的雾气, 盯着她说:“我就是想要等你,行吗?”
方才情绪波动太狠了,且惠整个人都显得份外不讲理,不懂得变通圆融。
又或许是极度矛盾下催生出的勇气。她重复了两遍, “不行,这不行的。”
沈宗良垂眸看她, 眼中风云突变,隔着不远的距离打量他,目光越来越沉。
对她,他好像总是有足够多的耐心。
浓密的云层被吹开,舒朗月色下,沈宗良嗓音倦哑地问:“这怎么就不行了呢?”
末了,他又找补上一句,“小惠,我不过担心你的安全。”
一句话就叫且惠的心陷入柔软而湿滑的沼泽里。
这种被人记挂的感觉很好,她喜欢,很喜欢。
但不应该是来自沈宗良。
她是福薄命舛的人,消受不起。
且惠今夜仿佛存心和他杠上。
只是她的语气很弱,“我很安全,打个车就回去了呀。”
沈宗良嗯了一声,笃定地让她现在就叫车子,“假使你打到了,我走。”
且惠忽然间泄了气,这里网约车进不来的,她一乱就给忘了。
她忽然低下头,像一朵从枝头坠落的白山茶花,凄婉、哀艳。
红砖绿瓦的倒影中,且惠小声道了句歉,“对不起,我太不识好歹了。”
人家来接她,于情于理她都该表示感谢的,反倒发起难来,不像话。
沈宗良面色冷静而温柔,看起来并没有被冒犯到。
他打开车门,声音漫不经心,“没事,上来。”
且惠点头,乖乖地坐上去,系好安全带。
刚落了点小雨,车窗上凝结一层薄薄雾气。
车子发动以后,且惠小心躲避着他的目光,指尖在玻璃上滑动。
但沈宗良还是一目了然地看见了她泛红的眼尾。
他默不作声,仍平稳地开着车,只是不再看她。
沈宗良自问没有抚平姑娘心事的好手腕,也不敢轻易起这个头。
他在等着她自己开口,也许她想说了,就会主动向他倾诉的。
如果不想,起码这个夜晚她也不那么糟糕。
想到这里沈宗良都发笑,他扶着方向盘,不可察觉地勾了一下唇。
他什么时候这么照顾过一个女孩子的小情绪?甘愿沦为陪衬。
解释不通,也许真应了唐纳言那句,你呀,鬼迷心窍。
终于且惠转过头,却是笑着的,“你的饭局结束了么?”
能看出来,她那个笑是很虚浮的,像悬在空中的尘粒,一吹就散了。
沈宗良开着车,只稍微扫了她一眼,说:“不想笑的时候,可以不用假装高兴。”
“我没有。”且惠下意识地反驳。
沈宗良拐过一个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忽然解了安全带。
她愣神的剎那,一只骨瓷般白净的手指伸过来,缓缓揩掉了她眼尾的泪。
果真,男人不管到多少岁都不晓得,女孩子脸上的泪不可以乱擦。
他指尖的温热熨帖着她的眼睛,很粗糙的舒服。
且惠就这么睁大了眼,在他浅褐色的瞳孔里望见自己。
柔红的眼底情绪复杂,匪夷所思、不敢置信,又有不可言说的慰足。
他这样一个漠然的人,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里,连细枝末叶都关注到了。
这算不算是他待她的与众不同里,又一份力证呢?
她犹如一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嫌疑人。
审判长一条一条地,口齿清晰地陈述罪名。
而喜欢上沈宗良,是她所有的明知故犯里,最重的一条罪。
她在心里绞尽脑汁地为自己开脱。
每反驳一句,就在心里多一分底气,这一局,并不全是她自作多情。
置身事外如沈总,也要为此负责。
沈宗良垂眼审视自己的手指,像审判自己踽踽独行的灵魂,神色专注。
没有人知道,在那一秒里他看见了什么。
是远处披绿的山坡,藏在楸树尽头的院子,路旁斜生出的杂草。
或者,只是衣衫单薄、一脸天真的钟且惠。
他两根指腹抵了抵,擦去了这份热意,“还说没有?你刚才在哭什么。”
且惠抽了张纸,迅速地抹了抹,“和冷双月说了一阵子话,有点伤感。”
沈宗良当然知道是哪档子陈年旧事。
他说:“觉得和她同病相怜?”
她下意识地点头,很快又摇了摇头,“不,她比我更难多了,也坚强多了。”
且惠不敢估计,换了是她在冷双月的位置上,会发生什么。
人生有一万种可能,却没有哪一种能够预知和置换。
“不要去比较,苦难没有什么好比较,也并不值得传颂。”他说。
沈宗良重新发动车子,他开得很慢,手腕从衬衫袖口捞出来,漏一截子白。
是的。且惠也这么想。
因为刚哭过,她带着浓重的鼻音,“我以为你这样的人,不会懂这些。”
沈宗良加重了语气,“我这样的人?”
“是啊,你们这样的人。”且惠假装听不出,继续说:“绝大多数的上位者,都无法共情普通人的挣扎,他们只有傲慢和庆幸,庆幸自己是如此的会投胎。”
这话真有点恃宠而骄的意味在了。
她胆子大了,什么话都敢往外蹦了,也不怕惹恼他。
岂料沈宗良不以为忤,反而笑道:“你这张嘴倒很会骂人。”
且惠也笑了,斜靠在真皮座椅上,歪了身子看他。
路灯一盏盏倒退,他的脸浮掠在半边光影之中,午夜的梦一样不真实。
沈宗良的鼻峰太高,眉骨也那么深,但压低眼睫时,竟有种温润的平和。
她忽然想,要是这条路走不到头就好了。
车开过东三环的高架,“金悦府”这三个字,又突兀地出现在眼前。
这一次且惠没有避,反而指给沈宗良看,“喏,我爸爸投资开发的小区。”
“嗯。”沈宗良余光带过一眼,“知道。”
她细细的指尖抓在皮垫上,兀自懊悔,“其实,我希望当年他没有挣这笔钱,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卷入冷家的事情里。我们一家人仍旧好好的,哪怕穷一点。”
“他还是会的。”
沈宗良镇定地开口,他说:“不管有没有尝到甜头,他都会掺和进去。”
且惠忽然坐正了,“为什么?”
妈妈从不与她谈当年的案子,仅仅告诉她不要对此发表过多的看法,爸爸就是做错了事。
她曾咬牙切齿地说,当年整个集团赔进去也是应该的,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光影变化里,沈宗良单手扶着方向盘,冷静对她说:“有人做局,就必须要有人入局。而部分人的加入,从一开始充当的角色,就是替罪羊,或者说是白手套。所以,一定会有人利诱你爸爸的,他也一定会去。这整件事,如果说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大概就是钟秘书太早过世了。要是他那时仍在,从旁点破一下你爸爸,兴许不至如此。”
他不失偏颇的口吻,像法官最后的结案陈词,冰冷而客观。
霎时间且惠懵了,类似的话她从没有听过。
陈老也好,董玉书也好,每一个人都不肯同她讲。
他们不愿告诉她丁点儿实情,由得她整日地假如来假如去,设想这样又设想那样。
但今天沈宗良告诉她,不管怎么样,结局都是早注定好的,没有可改的余地。
也许他残忍、冷酷,但这就是事实,而那些美好童真的幻想,根本不存在。
她最后的一丁点侥幸也折戟沉沙,如拨云雾见青天。
沉默良久,她才喃喃说了一句,“谢谢。”
还以为,她又要点评上一段尖酸话,原来不是。
话说出口,沈宗良其实是隐隐后悔的,为那一瞬间她苍白的脸色。
虽然这是一句实话。但实话有的时候,未必就要实说。
他出言安慰,“既然明白了前因后果,以后就不要再多想了。”
且惠哼的一声,“被您一说,悬着的心都已经死了,还能想什么呀。”
“......”
就......她的阴阳怪气永远不会迟到。
沈宗良似笑非笑,“但现在心情确实好点儿了?”
“好多了。走出了很多年都出不来的死胡同。”
且惠说完,肚子不听话地咕叽两声。
见他撇了一眼,她不好意思地瘪瘪嘴,“我没吃晚饭,饿的。”
沈宗良故作吃惊,“下午不是举了那么大串糖葫芦?”
她哎呀一声扭过身子,“我没有吃完,都扔掉了。”
沈宗良哦了句,学着她的软调子,“我以为像你这样的人,不肯浪费粮食的。”
他拖腔带调的那一下子让且惠想笑。
要死,不像个年长者的沈宗良,她更喜欢了。
且惠质问上他,一副不客气的样子,“欸,你说清楚,我是哪种人?”
她大起胆子凑到身前,沈宗良被拉扯进一团淡淡的香雾里,似乎是格兰维尔玫瑰。
仿佛只要答错半句,这个越不越不讲理的小姑娘,就要张牙舞爪到他身上来。
她在别人面前总是柔和的,眉头微锁,像二月初的湖畔烟柳,裹着一团未知情绪的轻雾。
和他独处时,那一点小孩心性才一点点释放出来。
很会回嘴,还很会呛人,也敢指使他爬树摘花,叫他站树下等着。
这一点微末的特别之处,竟让沈宗良感到十分受用,如同养了个不省事的妹妹。
但天可怜见,他那体弱的母亲,根本没条件给他添什么小妹,生下他已是万难。
唯一的一个侄女棠因,又怕他怕得要死,恨不得躲开他五里地。
沈宗良低笑一声,胡诌道:“就是像你这种特别有爱心,很喜欢小朋友的女孩子,我想,应该不舍得丢掉甜食的。”
“嗯。本来是不舍得的。”
她满意这个回答,脸上是得逞后的笑容,只是心如擂鼓。
为他居然如此地迁就自己,为车厢内过于浓厚的氛围。
“想吃什么?”
且惠一时没反应过来,“嗯?”
沈宗良说:“不是饿了吗?有没有特别想吃的?”
“有,小馄饨。”说完,且惠看了一眼时间,“不过这么晚了,小吃店应该都关门了。”
下一个路口,沈宗良平滑地转个弯,“没事,我带你去个地方。”
夜色里,他的神情在灰暗的光线下,难以辨明。
且惠雀跃着,用力地嗯了一下。
就让她短暂地享受这个夜晚,也许很市井,很琐碎。
但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必考虑。就只是被照料,被应承全部的想法,被宽纵一切的脾气。
且惠装模作样地当了太久大人了,都忘了自己才十九岁。
那时的她不懂得,再急促的人生也需要宕开一笔,用来呼吸,用来抒情。她只不过是发自本能的想要接受沈宗良的宠眷。
像一个久困于沙漠中的人,偶然淋到了一丁点儿小雨,恨不得跳上一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