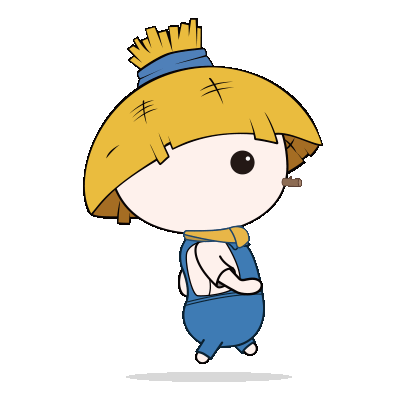这一晚, 且惠不知道是愧疚还是兴奋,缠着他问东问西,一直有古怪的题目从她嘴里冒出来。
令他想到他们在北戴河过的第一夜。
小女孩也是这样, 好像被设定了提问的程序,一直要他回答。
一室昏暗中,沈宗良拍着她的后背:“好了,安静,闭起眼睛睡觉, 以后再问。”
以后再问。以后这两个字好厉害,给且惠吃了颗定心丸。
她渐渐不再说了,毛茸茸的脑袋在他怀里拱动了两下,换了个姿势, 睡着了。
回江城之前,且惠抽了两小时的空,去山上看望陈云赓。
她下车后,提着礼物走了一段才到, 在门口就听见元伯的声音:“我会提醒陈老注意的,以后沾一点荤腥的吃食,就彻底和他无缘喽。”
原来是送了医生出来。
且惠站在台阶下, 朝他笑了笑:“元伯,这几年您好吗?”
元伯站在原地, 总觉得这个容貌出挑的女孩子他见过,名字到了嘴边,但就是说不出。他略带抱歉地说:“恕我眼拙,你是......”
她笑着上了一格:“我是且惠呀, 钟且惠。昨天打过电话的,还让您关照卡口。”
“哟, 且惠都长这么大了。但电话不是宗良打的吗?”元伯恍然悟过来,拍了拍脑门,“我还以为是他要来,这真的是......”
“是我让他打的,我找不着您号码了。”且惠往回廊里探了探脑袋,“爷爷在里面吗?”
元伯连连点头,“在,医生刚给他检查过,进来吧。”
碧空如洗,日光晒着大片金色的琉璃瓦,像投射在的平静的湖面上,浮光点点。廊下的花架上,密密匝匝的紫藤枝盛开如烟霞。
初夏的懋园一派生机,但它的主人却垂垂老矣。
陈云赓躺在黄杨木摇椅上,手里拈了串珠子,慢慢地、细细地看。
且惠叫了他一声,“陈爷爷。”
他在身边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戴上了眼镜才看清楚,“是小且惠啊,你总算肯来看爷爷了。”
且惠羞愧得坐在他身边,几度张口:“我......我......这几年都......太忙了。”
陈云赓点头:“你们年轻人都忙,我是没多少日子喽,不知道能见你几次。”
她听得心里不自在,劝道:“别说这种话,您身体这么好,比我还硬朗呢。”
“来,这么热的天过来,走累了吧?”陈云赓让人给她倒了一杯凉茶,抬了抬手,示意她喝。
且惠喝完,坐在他身边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谈她在英国的学习,在香港的工作,后来又为什么回了江城。
陈云赓听得很认真,他说:“除了上学,偶尔有一些课外活动吗?”
“有啊。”且惠挑了好玩的告诉他:“有空的时候也会去看赛马,七八月赛事充盈,每日镜报上有免费门票放送,可以自选时间城市和场地的。”
他点点头,“不错,你小时候喜欢骑马的。在那边交到新朋友没有?”
且惠坦言说交不到,“英国人呢,他们的礼节比谁都客套体面,但界限是很分明的。再说,我也不是个很外向的人,别人刚靠近我,还没开口呢,闻着味儿不对我就跑了。”
陈云赓被对她这个自我评价逗得哈哈大笑。
且惠捻了一块点心在指尖,也低头笑了。
她也讶异于自己今天的兴致。怎么说了这么多在英国的事情?连没信号的地铁,每天由专人点亮的煤气街灯,博物馆一年只展出六周的《女史箴图》,都提到了。
放在过去,这一部分她都是一笔带过的,不会超过两句,有时对方都回味不过来。
且惠盯着那块云片糕,她想,或许是因为她了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她去牛津念书,并不是一场见不得光的交换,而是她的爱人精心挑选的礼物。
陈云赓笑完,静默地喝了一口茶,忽然问:“自己的终身有什么打算吗?宗良应该很关心这件事。”
且惠让沈宗良打电话来,就没有要瞒老人家的意思,她说:“我就是想和他在一起,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陈云赓问:“你妈妈是什么意见?”
“一句好话都没有,沈家在她眼里是个虎穴,好像我进去了,就要被吃得骨头都找不到呢。”且惠老老实实地说,连个标点都没夸大。
“嗯。”陈云赓把手交迭放到小腹上,客观地说:“小沈夫人这个名号嘛,听起来就像是要吃苦头的,你妈妈也是以己度人。”
且惠心凉了一截。
完了,连陈爷爷这么练达的长者都不看好。
但过了会儿,陈云赓指了指屋檐下那几盆花,“且惠啊,你看那是什么?”
“像是栀子花吧。”且惠也没什么心思辨认,随口答了句。
他撑着坐起来,又拄着拐杖要走过去。
且惠赶紧上前扶住他,“那是您种的吗?”
陈云赓往上面洒了点水,“我每年都会种几盆,等到我老伴儿忌日的时候,送到她的墓前去。”
“可是栀子在北方很难养活呀。”且惠说。
陈云赓笑:“是呀,我们刚从南边回来的时候,所有人也都是这么告诉我老伴儿的,说栀子花适应酸性土壤,但北方连水质都偏碱性,养出的花苞发黄发硬,又说它不抗冻,低于十五度就要冻死。”
且惠托起一瓣花看了看,“但您养得真好,还很香呢。”
“这是我和她一起研究了好久的法子。”陈云赓放下喷水壶,和她一起坐到廊下,“两到三天浇一次水,晚上一定要挪到温室里,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调酸,硫酸亚铁两克,水两千克,最好再加三克白醋,稀释好了直接浇到土里。”
且惠还没听出门道,只是由衷地赞赏:“您和奶奶真恩爱,她喜欢的你也喜欢。”
“你错了,我不喜欢。”陈云赓笑着摆摆手,“我一个粗人,哪喜欢的来这些?但是我知道要团结好夫人,这是功课。”
她点点头,一副受教的模样。
但陈云赓不是要讲这些丈夫经,他说:“爷爷想告诉你,过来人的经验,就算是深刻的、痛苦的亲身经历,也许听起来再正确合理不过,但它放在你的身上,也不一定就适应。”
休息了片刻,他又指了一下香气浓郁的栀子:“你像这个花,连大院里的花匠都说没法子,但我还是栽活了,开花的那个清晨,整个院子里都是掸不开的香味,左邻右舍都跑来观赏,你爷爷还高兴地写了首诗。”
且惠听进去了,她大为震动,眼珠子亮晶晶的。她说:“您的意思是......”
“沈家这个二小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不是我偏心,非说他比人强。但这世上,能做得了他的主的人,我看还没有。你别说他妈妈了,就是忠常还在世,对他的事指手画脚多了,老二也是要光火的。”
且惠心里乱得很,她小声说:“他是什么脾气,我清楚。”
“那你更应该知道,他不会是你爸爸。可即便庸懦如你爸爸,你们还是有一段很好的日子。这样拿你父母的婚姻去套,公式错了,控制变量错了,结果当然也是错的,爷爷说的对吗?”陈云赓转过来看她,慈爱地问。
她拼命地点头。
陈云赓望了她很久,最后才拍了拍她的手背说:“好孩子,小时候受了那么大罪,长这么大了,你也稍微顺一顺自己,要不然太苦了。”
他说完,一直守在旁边的元伯就来扶他,“去休息吧,您今天说了太多话了。”
陈云赓点了一下头,二人往园子深处的卧房里去了。
且惠独自在廊檐下坐了很久,沾了一裙子的栀子香。
她失神地抬起头,伸手接住了一片从枝头落下的梧桐叶,嫩绿的叶子厚厚一片,手掌般的纹路清晰可见。
从十岁以后,她好像就在不停地赶路,思考怎么空手夺下生活的白刃,有时候真的很想歇一歇,暂时忘了自己的处境。
但这是不被董玉书允许的。
她不怪妈妈,只是遗憾因为亟待出人头地,而一再被矮化的生命体验。当其他人在环游世界、呼朋伴友甚至什么也不做,就只是虚掷光阴的时候,陪伴她的只有一张办公桌、一盏灯,和案头堆积如山的工作。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她活的一点也不成功,只是个不自由的可怜人。
//
且惠比沈宗良要晚两天到江城。
周四晚上,她在总部熬了个大夜,凌晨才从大楼里出来,请同事吃了一顿宵夜。
喝啤酒的时候,温长利玩笑说:“要是小钟能留下来就好了,整个部门的工作效率都上去了,明天我就跟沈董打报告,把你借调过来。”
“好啊,只要沈董一签字我就来。”且惠举着两串烤肉,应和他说。
她周五下午的航班,太阳落山了才到抵达。且惠推着行李箱走出来,看见半边天色都隐没在诡丽的红晕里。
沈宗良来接她,且惠看见他的车子,快步过去。
她看了看表,狐疑地瞄一眼他:“哪里有这么快开过来啊?你早退了吧。”
“今天在市里开会,一散会就过来了。”他开了车门,一把将她推进去。
且惠坐好了,等着他从另一边上来,就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他们在没关窗的车内接吻。
沈宗良担心她走了一路,力道也是紧一阵松一阵,不敢一直太大力。吻得重了,且惠就呼吸明显变得困难。稍松一松,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起来,不停打湿他的下巴,像没满月的小猫喝水一样。
后面的车没耐心地摁了摁喇叭。
沈宗良捏着她的后颈,让她停下来,“这位扰乱交通的小姐,该走了。”
且惠把额头贴在他手臂上,吃吃地笑。
笑了一会儿,她仰起脸,说:“好饿,我们去吃饭吧。”
沈宗良捏了捏她的手心说:“在北边没顾上,到你们江城吃点儿新鲜的。”
“不可能。”且惠表示她都已经吃过了,“我回来好几年了,这里没什么新的东西,都是老调重弹。”
他浮夸地反问:“噢,真的吗?会不会是你这个消费等级......”
“侬撒意思啦?”且惠骤然蹙起两弯眉毛,气道:“请问你在看不起谁呀?”
沈宗良忍不住笑了起来,矢口否认:“首先,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其次......”
且惠还在瞪着他,“还有其次?其次什么呀?”
沈宗良说:“叉腰的样子很可爱,以后多叉。”
很像一只强逞威风的小老虎,只可惜还幼年期。
她往下看了自己一眼,两只粉拳头果然抵在腰上。
且惠立马放下来,不自然地拍了拍手,又去拨头发,“才不叉呢,我是文化人。”
沈宗良把她的手握住,递到唇边亲了一下:“这两天在总部累着没有?”
且惠说:“还好,反正在哪儿都是卖苦力。我提醒你哦,温长利说要把我调过去,还想你同意呢。”
“人家讲笑的,不要把这些闲谈当真。记住了,除非正式找你谈话,否则都是假的。”他摇了摇头,又说起另外一件要紧事,“倒是这次信托副总的竞聘,关鹏说你连名都没有报,为什么?”
“我不想每天去应酬,再喝得醉醺醺回家,就为谈成个项目。”且惠仿佛已经预见到那种日子,嫌弃地说:“而且要和吴总搭班,我也不喜欢他这个人,所以就没考虑。”
沈宗良认真听完,面容语气都严肃起来:“我说两点,第一,在企业里做不出业绩,只是专业水准高,是很难出头的。况且,因为看不上某个人就放弃工作机会,孰轻孰重?”
“工作机会重。那第二呢?”且惠还有些不服气的,小声问。
他说:“你看主要部门的这些负责人,有几个没在业务条线待过?除非你打算一直当这个合规部副总,每天就写写材料看看合同,等小田退休了,你再接手干几年,那当我没说。”
她被教训得哑口无言。
且惠低了半天的头,有一下没一下的,揪着裙面上的水溶蕾丝。她说:“那我学的就是法律,我对合规工作是有感情的,你让我去做管理,我不行也不乐意。”
小姑娘对法律事业的这份执拗,让沈宗良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他几乎是恳求的口气:“我的小祖宗,只埋头钻业务是没用的,顶多评你个集团骨干,给你颁张奖状了不起!你非得学会怎么打理人事,才能一路走得顺,走得远,知道吗?”
“不知道。”且惠朝另一边扬起下巴,“我在律所的时候,就只要做好事情就好了呀,也没这么多名堂经。”
沈宗良反问她:“问题这是在瑞达吗?正相反,华江不是给你端着高知的架子谈理想的地方,没人会看重你有多热爱你的专业。在我和总部对你的综合考核表里,更没有一栏,是叫做情怀的。”
知道他是掏心掏肺为自己好。且惠也和他交了个底,“其实我当初来华江,是因缘际会,妈妈要人照顾,我不得不辞掉香港的工作。只是管业务还好,但人情往来什么的,我弄起来真的好吃力,好几次都想辞职了。”
在华江这两年,但凡男领导们开口要她陪着去应酬,且惠就觉得头大。
她宁可在办公室点灯看提交上来的法律合同。饭局上,她也很怕碰到那种交际尖子生,烘托得她自己好像很清高,察言观色、找机会敬酒、说奉承话这些,真的会要了她的命。而这份清高在大多数人眼里,前面是要加个假字的。
沈宗良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苦口婆心了这么多,小姑娘一句不想干了,就直接堵上了他的嘴。他说:“我要是把你放到华江证券去盯业绩,你不是更要叫天。”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沈宗良。”且惠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不停摇着他:“快点,快点说你没这个意思,快说呀。”
他余光瞥了她一眼,脸上流露出一股涓涓的柔情,无可奈何地笑了:“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想要保留本心,躲进象牙塔里搞搞学问,教几个学生,是这样?”
且惠说:“这个我没考虑好。幼圆都从学校出来了,她自己开了家传媒公司,很风生水起的。”
幼圆打辞职报告的时候,就对她说:“我还是太理想化了,以为学校会轻松一点,但事实上,没有了我爸爸,没有了冯小姐这个瞩目的身份,哪儿都不是避风港。人生的必修课是逃不脱的,你避过了这一次,下次还是会找上你,反反复复,直到你学会为止。”
她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沈宗良听。
他笑了笑,“连你的发小都悟出道来,躬身入世了。你还跟个孩子式的,在这里挑挑拣拣。”
且惠瞪着他:“这又不是点菜,点错了不吃也可以,这是工作呀。”
“好好好,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考虑好,我不干涉你的决定。”沈宗良拗不过她,把她的手拉过来,交代说:“想要在华江发展下去,你就参考我的意见。如果实在不喜欢,我再做别的安排,这样可以吗?”
她乖巧点头,很娇气地嗯了一声。
有种把一直买不到的糖果揣进口袋的心情。
无论进或退都有沈宗良给她兜着。
这样还不可以的话,她也太难伺候了一点。
车子开上高架,夜幕渐渐温柔地拢下来,远处耸入云端的高楼沉静而肃穆,晚风裹挟着一阵香气吹进车内。
且惠转过头看他,稀薄的光线括出沈宗良影影绰绰的下颌,像一幅朦胧的人物画像。
一时间,她突然觉得,那种不管做什么身后都有靠山的感觉,又回来了。
那一年春月夜,她拉着箱子走出西平巷,绝望地以为自己失去了这个世上仅有的庇护。但飘飘荡荡过了六年,她好像又可以在这个马不停蹄的世界里,偶尔松松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