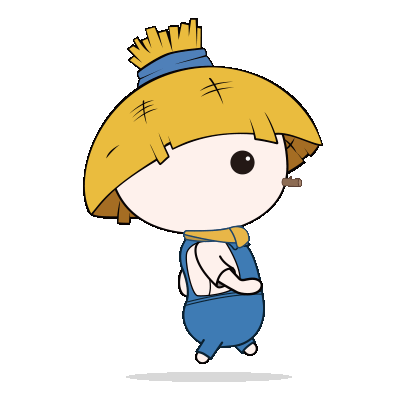一场漫长的隆冬过后, 凛冽刺骨的寒风收了势头,春花杨柳次第渐开。
在大四下学期紧张激烈的申请季里,三月十六号那天,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她坐在书桌前,看见学校的portal上显示了offer,到八点半收到邮件,她反反复复读了一遍又一遍, 脸上冰凉的表情,像看一封病危通知书。
她紧抓着的这些空中楼阁般的日子,对沈宗良的仰慕、迷恋和挚爱,最终以牛津的MJur offer落下了一道越不过的高山, 山那头风光再好,但浮云遮望眼,她永远也攀不过去了。
且惠走到窗边,翠绿的竹枝轻轻晃动在日头里, 扑在脸上的风也温温热热的。
她麻木着一张脸,已经为离别哭过太多次,在那么多个被他抱着入睡的夜里。她安静地落泪, 又安静地擦干,再吻一吻他的脸。到现在, 已经没有眼泪可流。
她站了很久,沾了一身青翠的竹叶香,最后也只是沉默地转身,不再看了。
且惠在衣帽间取下自己的箱子, 当初来这里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东西,那些精美的华服高珠, 都是沈宗良送的,她也没打算带走。
她收拾得很快,两只箱子塞下了全部的行李,并排放在中间的玻璃岛台旁。
且惠出了卧室,她如常去餐厅吃饭。往日里总要讨价还价的人,今天一碗补汤喝得干干净净。
看得隋姨叫奇,前天夜里吃晚饭,老二还“好孩子、好姑娘”的叫着,把人抱在腿上哄了大半日。春寒料峭的天,累得他头上的汗都出来了,且惠也才只喝了半碗,咽不下去,捂着嘴,生气地跑掉了。
她收拾碗筷,朝且惠开怀一笑:“今天真是立了大功了,等晚上老二回来知道,一定高兴。”
且惠笑笑,忽然郑重其事地说:“隋姨,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别太操心了。沈宗良又不是天天在家,你偶尔也可以偷偷懒的,总是那么舍己做什么。”
隋姨没听出所以然,还当且惠是灵光一冒的关心。她说:“还是姑娘家疼人,老二从来不会讲这些的,张嘴就是问这问那。”
她点头,“嗯,我回去午休啦。”
这阵子她闲下来,沈宗良反而忙得脚不沾地,夜以继日地操劳。
且惠准备好等他到深夜的,看书看累了,歪着身子,躺在竹榻上睡了过去。
但没料到,他今天回来的蛮早。
只是不知道在哪里操劳了来,一进门就嚷饿叫累的。
隋姨忙说:“厨房蒸上了七星斑,我先给你端来?”
沈宗良往正厅里一坐,边脱了外套,“大白天光的,就不吃沾鱼腥了。下点素面吧,小惠呢?”
她往东边努了努嘴:“在书房里,我弄那些竹子的时候,看见她在用功。”
吃了几筷子面,沈宗良回了卧室洗澡。
上面派了钦差来集团搞调研,偏偏邵成钢不在,去山西视察合资项目去了,只好他来主持座谈会,汇报上一年度的系列工作,代表东远作表态发言。应承了三四天了,到今天开完大会,才算了了事。
送走调研团时,沈宗良领着几位高层进了电梯,长出了口气,闭着眼扯松了领带,又解掉了一颗扣子。
连郑副总都笑了,“宗良啊,这比监管具体业务还要更累多了吧?等过两天老邵回来,还要再传达一遍上面的指示精神。”
沈宗良勾了下唇角,淡嗤了声。
他扬了扬手里的文件,“总而言之一句话,既要创利增收,又要管头管脚。是得让董事长也听听,不能光叫咱们几个头疼。”
他洗完出来,又绕去书房看且惠。
窗边春风浩荡,她手里抱了一本书,歪在长榻上睡熟了,只是眉心微蹙,双唇紧抿着,像在梦里也不快活似的。
沈宗良没有吵她,坐到了桌边,打算回复一下导师的邮件。
前几天他老人家说,想要邀请他回校去演讲,电子请柬已经发给他了。他的护照早就交给了行政部,去美国的审批手续也太麻烦,沈宗良正要委婉地拒绝。
他一唤醒屏幕,抬头就是牛津醒目的校徽,再下一行,是“Certificate of Offer“的标题,至于下面的details,他不想再读了。
沈宗良看了一眼睡着的且惠,有无数的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一个比一个更危险。
他有些紧张的,从最底下一格抽屉里摸出包烟,急不可待地拆开包装,点上以后深吁了一口,才夹在手里,慢慢靠在了身侧的乌木扶手上,仿佛靠着这口烟活了过来。
小惠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学校?
如果是正常念书,不至于瞒得这么死,连他都不透露半句。
还是说,她预备远走高飞以后,就不再和他交往了。
他烦躁地抽掉两根烟,连连否认自己的想法。
不会的,小姑娘昨天还在说爱他,哪里即刻就要走呢。
或许,她是随便试一试,在没录取之前不敢说,怕被他知道了笑话。
且惠是嗅着这股沉香味醒来的。
他们住在一起后,沈宗良从不在室内抽烟,她对这味道感到陌生。
她掀开身上的毯子,把书放在竹榻上,揉了揉眼睛,“你回来了。”
但沈宗良没说话,他沉默地抽着手里的烟,隔着一团白雾看过来。
且惠坐到他对面去,眼睛瞄了一眼电脑,“你看到了。”
“嗯。”沈宗良落落寡欢地,点了个头,“没看到的话,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
她拨着笔架上的一排羊毫,“也是今天,沈宗良,我有话要说。”
沈宗良心里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你说,我听着。”
且惠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后面的书架上,“我们分手吧。”
冷不丁的,手里那段烟烧到头了,火星子燎上他的手。
沈宗良被猛地烫了一下,着急忙慌地摁灭了,又去拿桌上那杯冷茶浇手,凉得透了,才抬起眼皮看她,“刚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且惠忍了忍,按捺住上前看他伤口的心情。
她冷冷地重复了遍,“我说,我要和你分手。”
沈宗良面上一冷,指了下电脑,“因为要去英国读书吗?”
“不是。”且惠摇摇头,“很早之前,我就打算要和你分手了。”
他心脏突地快跳了一下,失态地哽了哽。
沈宗良说:“说清楚点,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且惠一字一顿地说:“意思就是,我不喜欢你了,干脆用你做了一笔交易,和你的妈妈。你知道,牛津法学院很少有奖学金的,但她会给我一笔钱。”
呵。是这么个曲折的故事。
只消一句话,沈宗良就明白过来,自己大势已去了。绝望和灰心漫上心头,情绪仿佛一只穷凶极恶的野兽,在一瞬间咬住了他脆弱的血管。
他的太阳穴扑扑跳着,手上仍有条不紊的,拨正刚才洗手的茶盏。
沈宗良慢条斯理地问她,“你缺钱怎么不来和我说,我不能付给你吗?”
原因他并非猜不到。这么卑微的明知故问,已经是僭越了他的骄傲。
大概就是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包括他的钱、他的人脉都不想要,才选择直接找上姚小姐。
但他还是尽可能的,对她无原则无底线地服软,做最后的争取。
且惠笑了下,和从前一样天真地拿水画着圈,“拿了你家的钱,就好不再和你有瓜葛了呀。”
这是沈宗良最喜欢的样子。
到了这个时候,嘴里说着这么伤人的话,她还敢做这副模样出来。
他气极了,反而冷冷地笑起来,“是她主动找上你的,对吗?”
沈宗良想要她说是,穷途末路了,他仍对他精心娇养过的女孩抱有一丝希望,如果是出于姚小姐的逼迫,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权衡之后选择了自己的前程,他无话可说。
且惠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表演出了问题。
她也不知道,沈宗良那么聪明,是否猜中了事情的真相。
但已经没有退路了,她说:“我找你妈妈的,没想到她这么好说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很好,他最后一点期许也被她无情地点破了。
什么叫多余一问,这就是。
沈宗良气得一阵晕眩,眼前黑了黑。
他撑着桌子,紧闭了会儿眼,再睁开时,还是温柔地挽留她,“小惠,是不是我最近太忙,疏忽你了,等过一阵子,我带你去......”
且惠看着他这样子,心上像被一把尖刀剜出了个洞,怎么都缝合不起来,身上的血都冷得凝固了,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说了这么该死的话,沈宗良应该大发雷霆才对。
他有这么爱她吗?为什么总在给她找借口。
且惠咬了下嘴唇,“和那些都没有关系,我就是不爱你了。”
他冷白的手指点了点桌面,“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哪一个月,哪一天,哪一分钟。”
沈宗良觉得自己应该是疯了。
按他的脾气,不管对面坐着的是什么人,在说出这些话以后,他也应该立刻起身,拿出他一贯的做派来,把她的东西丢出去,让她滚远一点。
但他没有,他在低声下气地追问原因。
且惠回避着他的目光,说:“这很重要吗?”
他笑了下,“对我来说很重要,下次谈恋爱我也好吸取教训,对吧?”
她只好把那套说辞原封不动地搬出来。
且惠说:“非要我说这么清楚吗?杨雨濛不是早就提醒你,我混迹在公子哥儿当中,就是攀高枝去的,你是我选中的目标而已。我只能说,你以后再要找女朋友,眼睛放亮一点。”
他自嘲似般地哂笑了下,“她曾经特地来找我,举了很多事例证明你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她还说,你提前搬去报社大院,是因为早知道我要去,是这样吗?”
他们一个问一个答,隔了张油润褐红的长书桌对峙,气氛安静诡谲。
末了,且惠五味杂陈地艰难扯动着嘴角,“就是这样,你相信她说的就好了。”
沈宗良轻慢地勾了勾唇,“是吗?”
他并不认为,浅薄张扬如杨雨濛,她说出来的话,有什么信的必要。
但且惠笃定的神情,一句句回答像匕首,尖头向内,刺进他的心里,他的身体被扎得千疮百孔,血肉模糊。连他自己都怀疑,真的有那么痛心吗?为什么手指都抖起来。尽管这样,他还得镇定淡然地坐在她面前,勉力维持风度。
且惠抿出一个再鄙薄不过的笑,她说:“人们最爱追逐的,不就是钱财富贵吗?再不然,就是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你我都在彼此身上得到了,大家一样俗不可耐。”
到这里为止,沈宗良已经没话好对她讲了。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她竟然用了俗不可耐这四个字。
她就这么形容他们的关系。
他点头,“清楚了,我会的。牛津很好,祝你前程似锦。”
最后一点仅剩的自尊,也不允许他再继续下去了。
且惠站起来,转身前,她说了句,“嗯,谢谢您这两年的关照,再见。”
呼。还好在这里结束了。
为什么比她想象得要久多了,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还在文质彬彬地祝福她?沈宗良还不如把杯子摔过来,再痛骂她两句。
这么强压着火气,且惠真怕他的身体出问题。
但她什么也不能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脸上的表情出卖自己。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一轮莹白的满月升了起来,照在幽静的胡同里。
滑轮和地面摩擦着,发出沉闷轰隆的声响。这个地方,她一无所有地来,又一无所有地走。
且惠抬起头,很努力地睁圆了眼睛,才把眼泪逼回去。
她不想再哭了。
为沈宗良没有必要,他冷静而自知,克制力极强,不会过分停留在男女之事上的,也许睡上两觉就好了。
为她自己,就更不必了。
只是未来的路那么长,一想到再也没有人会像沈宗良一样,会把险恶都挡到她的身后,护着她在世上畅通无阻地前行,还是不免难过。
且惠牵了牵唇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推着箱子消失在了路口。
她走后不久,书房里就叮咣乱撞的,传出一阵摔摔打打的声音。
隋姨跑过去看,是一向沉稳有礼的沈宗良一脚踹翻了书桌。
进去时,看见他的手搭在胯上,拿着手机骂道:“您瞒得我好啊!”
王姨在那头不停地喊冤,“那天她就来坐了一会儿,夫人还把我支开了,我真的不知道她们说了什么,后来才晓得,是关于她留学的事情。”
沈宗良质问道:“那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王姨叹声气,“我跟你说了又能怎么样?老二,人家死活要走,你也拦不住。就算留住了,心也不在你这里了。我说句不知身份的话,她就是拿你当垫脚的门板了,亏得你那么疼她。”
他闭了闭眼,挂断后,把手机掼在了地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