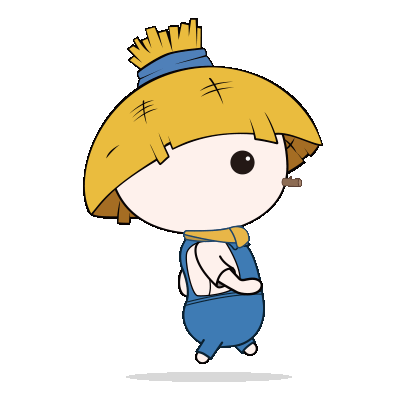午后云淡光薄, 且惠手里摇着枝绿叶,在他身后慢慢走。
沈宗良听着草丛窸窣,有意放缓了脚步, 但还是不见她追上来。
这姑娘走路也是够慢的。他这么想着,回头看了一眼她。
哪知道人根本没动,就那么定在一棵树下,仰着头,附庸风雅地赏花呢。
沈宗良倒了几步回去, 站到她身后:“在看什么?”
且惠指了指头上,答非所问:“想不到这里居然有。”
沈宗良对花知之甚少,唯一的交流就是吩咐秘书,定时送一束给他母亲。
他啧了一声, “也不很香,怪蓝的。”
对于这么奇怪的形容,且惠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她说:“它就叫蓝楹花树啊。”
说完, 她转过头冲他提要求,“麻烦你,帮我摘一枝下来好吗?”
沈宗良目测了一下距离, “眼前就有,你自己摘不到吗?”
且惠托起他的手腕, 恳求的口气,“这枝不好,我想要那一大丛,可不可以?”
“那得爬树上去!你有那么喜欢吗?就非它不可了?”
她双手合十, 很虔诚地点头,“是的, 我有。”
沈宗良垂眸看她一眼,有些无奈的,扶稳了树干就往上爬。
这都小时候干的事儿了,长久不练,他还真有点怕跌份子。
因此,在上树之前,沈宗良胸前很明显一道起落的脉息,像在酝酿什么。
那个使唤他的人,在他攀上树梢的那一刻,很有良心地在树下喊:“小心啊。”
沈宗良没法子,就近掰下一大团,丢下去。
且惠从草坪上捡起来,喜滋滋的,“就是这个,谢谢小叔叔!”
他顺利落下来,拍了拍掌心里的花粉,阴阳怪气,“没事,大侄女高兴就好。”
可人家的眼睛一直在花枝上,根本就没听见,就连谢谢也是不怎么走心的。
沈宗良觑着她笑出的两点梨涡,盛着小女孩独有的稚气和纯真。
他也没有忍住,带着气哼笑了一声,拉过她的手腕,“走了。”
且惠被他带着往前走,这才想起来问:“刚才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里太大,我怕你走丢,”沈宗良停顿了一下,“毕竟是我带你出来的。”
且惠说:“不会,我记得回去的路。”
“噢,是吗?”他忽然停了下来,松开她,“那你指个路。”
她站在远处,手掌搭在眉骨处望了望,胡乱一戳:“呃,那边。”
“跟上我,走快点。”
沈宗良重新拉过她,大步流星的,朝另外一边走去。
“......”
他们到的时候,大家伙儿都已经玩累了,三三两两地坐在伞下。
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杨雨濛,她是第一个看到的。
沈棠因还在和庄齐说话,她拍着桌子就站起来了,低低骂了一句。
且惠抬头的瞬间,看见数不清的目光从前方投来,落在她被沈宗良握着的手腕上。
她赶紧挣了下,又恢复了拘谨模样,小心翼翼叫了句沈总。
沈宗良倒是一脸的坦荡,冷淡地松开她,总算能撂了差事的样子。
他面无表情地扬了扬下巴,“好了,去玩儿你的吧。”
“嗯,谢谢你帮我摘花。”
且惠感激地点了下头,怀里抱着她的战利品,飞快地走到幼圆身边。
好事的人太多,都伸长了耳朵听她们说什么,冯幼圆对这些心思了如指掌。
但这是且惠的事,不管对方是不是沈宗良,她都没义务要分享。
所以她什么也不问,只是接过且惠的花:“好漂亮,回家插起来。”
且惠拧开瓶水喝了一口,“是啊,就用那个白釉瓶插好了。”
“嗯,一会儿回去,就这么办。”
等着听八卦的人扑了个空,心里腹诽这姐俩儿嘴真严。
杨雨濛气得牙根痒痒:“我说什么来着?人钟小姐有的是手段。”
沈棠因环视一圈:“别胡说了。也不怕人看笑话。”
这时,一个服务生端来一份沙拉,位置太窄,不小心碰到了杨雨濛肩膀。
她当场发飙,“你干什么?这么不小心!”
服务生连忙道歉,“不好意思杨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杨雨濛不依不饶地说:“不是故意的你就可以弄脏我衣服吗?”
“这好像也没有弄脏吧?有必要大呼小叫的吗?”
冯幼圆撇了一眼她的白色针织衫,很看不惯地说。
杨雨濛回头,狠狠刮了她们两个一眼:“又关你什么事啊?”
那一下子,且惠目睹了她眼里蹦出的凶光,确定她是冲自己来的。
杨雨濛的眼神盯死了她,长久的敌对之下,也只看得见她眸中的坚韧。
那张温柔知性的脸上,不见半点犹豫退却,反而是轻蔑。
一种明知道对方在气什么,也不想多解释半句的蔑视,由得你炮火纷飞。
要说从小到大,钟且惠哪里最令她讨厌,就在于这点上。
小时候也就算了,不知道她现在还有什么好高傲的!
庄齐拉了雨濛坐下,劝了两句:“好了,大家都是同学,你这像什么话啊。”
沈棠因用眼神示意服务生下去,不必站在这里了。
闹了这么一出,再坐着也没什么意思,都纷纷打道回府。
走去停车场的路上,魏晋丰小声说:“想不到嘿,杨雨濛醋劲儿还这么大。”
“这八字还没一撇,她就不许沈总和人亲近了,要是订婚了还了得?”
魏晋丰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看他们订不了婚,近几年杨家行市不行了。”
看庄新华不吱声,沉默地走着路,他又勾肩搭背地说:“我就说且惠不简单,老沈是什么人,还能去给她摘花呢!”
雷谦明笑:“且惠要想拿下谁,那真是轻而易举。身上没什么定力的,单听她说上两句话,骨头就轻了。”
到停车场了,庄新华拨开他俩的手,“老说一件事儿,你们烦不烦哪?”
前头且惠没站多远,就在他们车边,不偏不倚地听见这句。
她抱着臂,扭头冲谦明来了句:“雷少爷,我大活人就在这儿,您指着我说多过瘾。”
“哎唷,对不住对不住。”
撞枪口上了,雷谦明笑嘻嘻地冲她作揖赔礼,“当我嘴碎,瞎说的。”
此刻沈宗良倒车出来,开了窗,停在路边等着唐纳言。
就听见且惠在生气,“好嘛,我清汤寡水地活着,到你们嘴里,被造谣成花蝴蝶了!”
在江城待得久了,她这不伦不类的京腔听得沈宗良想笑。
他就知道,在他面前的毕恭毕敬都是装出来的,这才是她呢。
果真,且惠在注意到他的瞬间,抱着的手臂就放了下来,规规矩矩地点了一个头。
沈宗良坐在车里,淡嗤了一下,旋即转开了视线。
直到唐纳言坐上来,他踩下油门,缓缓开出了球场。
唐纳言歇了一下,喝了半瓶水,说:“沈总一场球也没打,净哄小姑娘了。”
沈宗良单手扶着方向盘,心情不错地勾唇,“我要下场开盘了,你们还打什么?”
“别太狂了啊,等我练个三年五年的。”
他根本不信,“你去球场是奔着练球去的?哪回不是谈事儿,一谈就是三个小时,这能练出什么好球来?”
唐纳言被噎得不轻,他说:“合着好脾气全留给了小姑娘,跟兄弟就这么针针见血是吧?”
沈宗良斜乜他一眼,“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对她脾气好?”
副驾上的人笑:“看没人理她,硬是带着走了那么远路,还给人摘了老鲜艳的一枝花,这叫不好?”
“别提了。”沈宗良摆了摆手,说:“我以为这丫头有心事,怕她钻了牛角尖,哪知道根本没有,还能使唤我去爬树呢。”
唐纳言故意挑话说:“她钻她的,就算是最后命不济,那又关你什么事儿?你也从来不在女人身上用心的,不晓得多少人折你身上了!”
这么两句话还激不着沈宗良。
他开着车,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最后,到唐纳言都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他才轻叹了声:“总觉得她可惜了。”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且惠的过去还是将来。
见唐纳言手架在车窗上,盯着他,盯得说话的人心里发毛。
沈宗良命他开口:“别搞欲言又止那一套,有话直说。”
唐纳言笑,“还是那句话。我真不敢相信,你沈某人还能修出一副慈悲心肠,是不是上年纪了?”
这回沈宗良没否认。他挑了一下眉,“也许吧。”
当天晚上,且惠在冯家的园子里吃饭,和幼圆两个人。
冯校长两口子都不在,厨师特意来问了且惠:“钟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且惠已经洗了澡,她坐在桌边复习刑法,说都可以,只要不麻烦到你。
从回来就睡到日落的冯幼圆终于走下楼来,身上的轻纱拖到地上。
她索性脱了,换了条薄毯子裹着,在沙发上伸个懒腰。
幼圆问她,“我睡很久了啊?”
且惠的长发用根簪子挽了,松松地垂着。
她低头刷刷写字,“反正你自打进了这屋,就没清醒过。”
幼圆隔着长桌喊话,“是啊,我险些忘记问你了,跟沈宗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你们怎么是牵着手回来的?”
且惠她亮出手腕来比了比,“看清了啊,他抓得是我的腕子,和牵手差了十万八千里。因为我走路太慢,他嫌耽误。”
幼圆觉得她不老实,“是吗?我怎么那么不信!嫌烦带你去散步。”
“我也不晓得他一开始什么想法。”她手里转着笔,跟幼圆分析起来,“但你知道,他最后那个表情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幼圆凑近了,趴靠在沙发椅背上。
且惠笃定而自知的口吻,“他一定在想,终于把我这活爹送走了。”
“......不是,你都做什么了?”
“就是让他爬树呀。喏,花我都已经插上了。”
幼圆啊的睁大了眼睛,“不会吧?那是沈宗良啊我的天,你奴役他啊!”
她用了这么夸张且封建的词汇。
且惠有些心虚地问:“沈宗良怎么了嘛?什么人呀他是!”
冯幼圆想也没想,“一个注定一辈子坐在神台上的人。”
至少她们这圈小女生都是这么认为的。
她们能随时随地拿庄新华作筏子,敢挖苦魏晋丰,偶尔也能够讲一讲唐纳言的笑话。
却绝没有哪一个,敢对沈宗良有一言半语的不敬,即便是私底下。
沈宗良那副孤寡样,就注定了他不适合被拿来玩笑,也无人敢开他玩笑。
“......夸张。”
且惠用笔杆撑下巴,也后悔不迭的样子,“我当时就、就太想要这个花了嘛,没有考虑那么多。”
“行吧。”幼圆停了停,说:“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
“说。”
幼圆对着头顶的灯发了个誓,“你知道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无条件站你。但我得享有全部的知情权。”
且惠哎唷了一下,“我和他能有什么呀,真能扯。”
“不管,你答应我。”
“答应答应。”
第二天要去学校,且惠没在冯家久留,吃完饭就回去了。
她背着包,打袁奶奶家过时,看见她孙子抱着奥赛书出来,说要去找老师。
且惠半躬着身体,手搭在膝盖上问:“丁丁,是哪道题不会啊?”
小胖丁指了一行给她看:“就这个,姐姐你会做吗?”
“会啊。”且惠读完题就冲他笑,拉着他坐到石桌边,“我教你。”
袁奶奶走出来,催促着他,“怎么还不上车啊?司机等你呢。”
胖丁坐在院子里,举起书告诉奶奶,“不用去了,钟姐姐比老师讲得好,讲得妙!”
被童言童语这么夸,她还有点不好意思,站起来笑了笑。
袁奶奶手里拿着孙子的外套,说:“我一个老太婆也教不出,还准备送去他班主任那里,谢谢你啊且惠。”
她儿子儿媳都在宁省,胖丁留在京里读小学,平时都是袁奶奶照应。
另外,家里有一个做饭的阿姨,和专门接送孩子的司机,是她儿子上任前安排好的。
且惠摆摆手,“没事,教个作业而已。”
袁奶奶说:“这两天啊,我就让陈校长去给他请个家教,省了往外跑。”
“那样最好了。”她了一下头,提议说:“但今天的话,不如到我那里写作业?天快黑了,来来去去的不方便。”
他奶奶还在思量的时候,胖丁已经高兴地蹦起来:“好,我要去姐姐那里。”
袁奶奶只好答应:“那你要乖一点,不许吵到姐姐学习。”
且惠抿了抿唇,“不会,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那真是麻烦你了,且惠。”
“没事儿的奶奶,我正好有个伴,您快点进去吧。做完以后我送他回来。”
且惠领着胖丁进门,家里没有这么大的拖鞋,她说:“就这么进吧,不用脱。”
胖丁走进来,被眼前的场景惊着了一下,茶几上堆着的书也太高了,那么厚一摞。
如果不小心砸下来的话,应该能把他给就地埋了。
他不禁打了个抖:“姐姐,这些都是你的啊?”
且惠说:“是啊,那边资料有点多,你来坐这儿。”
她收拾出长餐桌,和胖丁面对面坐了,她复习法考,他则专心写习题册。
时不时的,碰到不懂的地方,小学生就来请教她。
半路且惠去切了个橙子,削了皮,把黄澄澄的果肉摆好。
她端给胖丁,同时递过纸巾盒:“来,小竞赛生,补充点维C。”
“嗯,姐姐,你帮我检查一下吧。”
“好的。”
且惠很仔细地看过去,比起他们读三年级时来说,题目的难度又上了一层楼。
她检查完,把两道错题给他讲了一遍,问胖丁懂了没有?
小男孩点头,有点懵懂茫然地问:“姐姐,我好累啊。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还只有丁点大的时候,且惠也不知道,家里都那么有钱了,她怎么不能痛快地玩?
董玉书还要逼着她上电视,参加比赛,做一切她认为有必要的事情。
且惠很不理解,为这个没少起争执,说这违背了她意愿,妈妈真是太专横了。
直到后来钟家落败了,是且惠自己忽然意识到,她只有读书一条路了。
她必须要自立,早一天从妈妈手里接过家庭的重担。
是形势逼她,是现实残忍地教会她,抽了她两个耳刮子后,命令她清醒一点。
真希望小胖丁不会有这一天,永远不要有。
瀑布般飞流直下的命运,足以淹灭每个人的意志。
对于无情地被冲到最下游的人来说,那份绝望是滔天的。
所以且惠只扶着他的手臂说:“我想,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