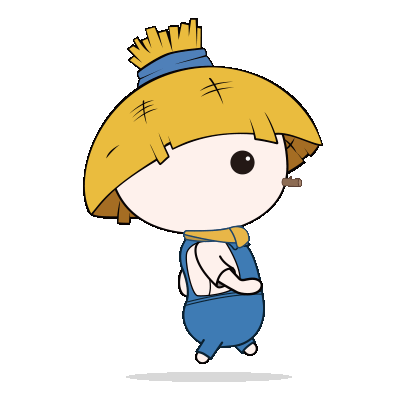这莽撞的一问, 连陈云赓都起了疑。
他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想是二人有些有什么故事。
但顾虑小姑娘的脸面,没当着这么多人硬问。
唐纳言受人之托, 不敢多说,“不要紧,已经去过医院了。”
“哦。”且惠看徐懋朝盯着她,连庄新华也看了过来,这才觉得不妥, “没事就好。”
雷谦明先举了杯,替她圆过去,“祝陈爷爷身体康健,长命百岁。”
一群人呼啦啦站起来, 陈云赓笑着受了,“好好好,我活一百岁,看着你们长大成人。”
胡峰又单独敬了敬, “爷爷,涣之在德国回不来,我再替他敬您一杯。”
“好。”陈云赓喝了半口白的, “他是匹没笼头的马,不如你听话。”
“哪儿啊, 我是没本事,我爸知道我的斤两,也懒得为我操心。”
这话让在座的都笑了起来。
只有且惠双眼空洞,视线落在墙角插瓶的红梅上。
这群人当中, 数唐纳言的辈分高一些,敢开开玩笑。
他说:“那也不一定, 咱们这儿也有安排过了,又被学校开除送回来的。”
徐懋朝也不敢发火,拜了拜说:“纳言哥,饶了我行吗?”
“可以啊。”胡峰和他碰了碰杯,“现在被你老子规训的,修养这么好了。”
徐懋朝笑说:“这算什么!修养好是因为被骂多了,你还没听小叔叔怎么说的。”
“他怎么骂的?我们也想听听。”沈棠因说。
“小叔叔说啊,我被开除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再野鸡的大学也有门槛,不是什么酒囊饭袋都收的,更不是见了钱就眼开,以后少诋毁人家。”
他说话的语气拿捏的很像,沈宗良那种不可一世的傲劲儿,和讲话时五六分的诙谐,刚刚好。
大家哄笑成一团的时候,且惠也低头抿了下唇,这很像他。
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生她的气到哪个地步了,身体受了什么程度的伤,这二者都在心里盘桓不去。
吃完饭,且惠被陈云赓单独叫住。
她没推辞,趁着夜色好,扶着陈老去园子里走一走。
园中草木茂盛,即便在隆冬也满眼青绿,点缀着一院的星光。
陈云赓状似不经意地问:“一晚上了,我看你都心不在焉的,怎么了?”
且惠自然不敢说实话。
她半真半假地问:“有一桩疑难杂症,爷爷。我好像走在一条越来越黑的路上,尽头在哪儿我看不到,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陈云赓笑了笑,“你爷爷给我当秘书的时候,写过一篇社论很有名。里面有一句话,刚好可以讲给你听。”
且惠扶着他在水亭里坐下,“什么呀?”
陈云赓说:“他说,其实终点在哪里,路会走成什么样,并不是那么重要,完全不必提前预设困境,因为走下去你一定会知道的。只要是自己选的路,就不必后悔。”
她点头,小声复述了一遍,“是自己选的,就不要后悔。”
说完,且惠展颜朝陈云赓笑了,“谢谢爷爷。”
陈云赓嗯了声,“不早了,让司机送你回去。”
“好啊。”且惠快速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正好幼圆先回去了。”
她随元伯穿过那道空廊,看见唐纳言站在栓马柱前抽烟。
且惠想了想,对元伯说:“不用派司机送我了,太麻烦了,我坐纳言哥的车。”
大门口的唐纳言听见她这么说,愣了一下。
这丫头怎么亲近上他了?是有什么目的吧。
但且惠客气地询问:“纳言哥,你能送我回去吗?”
他踩灭了烟,“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上来吧。”
她说声谢谢,弯腰坐在了后座上。
唐纳言扶着车门想了想,还是坐上了副驾驶。
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避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没办法,老沈太看重这个小姑娘,可以说是毫无原则地宠,宠得没一点谱儿了。人家把他轰出来,他还照着一日三餐让隋姨去送药送点心,电话也没少打。连周覆都无奈地说,嘘寒问暖到这种程度的话,不如直接用八抬大轿抬回来算了,是要累死谁啊。
唐纳言考虑了一下,要是被他知道钟且惠和自己一起下了山,而且就坐在他的手边,没多远的距离,说不定会引火烧身,他不能留下这点祸根子。
这些小九九,且惠当然想不到。
她规矩地坐着,问唐纳言说:“沈宗良他在家吗?”
唐纳言手上回着妹妹的消息,一时没设防。
他脱口而出,“躺着呢,他那伤势现在也走不了路。”
哪知道且惠大惊失色,她忽然提了提音量,扶着前排座椅,身体完全倾上去,“怎么,这还叫不严重吗?!他到底怎么弄的,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当心。”
这么大年纪是多大年纪?他和沈宗良一边儿大,唐纳言感到有点被冒犯了。
记得以前且惠也不这样,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玩笑也能让人听出是玩笑。想必,这又是被沈总娇惯出来的毛病了,整日整夜地由着她胡说,指不定还要哄着她任性骄矜一点。
唐纳言收了手机,回头跟她说:“今天去工厂检查,一整块的钢板没吊稳,掉了下来,老沈扑过去把那个工人救了。工人没事,他的腰受了伤。”
“他这个人真是,真是......”
且惠实在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了,指甲在皮垫上胡乱抓着。
可这是救人,她也不能不识大体,当着唐纳言的面,说些不应该的话。
唐纳言看她这副焦心的样子,也不像是要和老沈分开的。
那么,这段时间的冷淡疏远,全是在闹意气了。
看沈宗良身体不舒服了,也没心思再同他生闲气。
他趁热打铁问了句:“且惠,要不然我送你过去看看他?”
过了会儿他才听见且惠的回答。她说:“嗯,麻烦了。”
唐纳言点点头,“不麻烦,我也要再过去一趟的。”
西平巷里没有点灯的习惯,到了夜晚总是黑沉沉的。
粗壮的榕树隐在月影里,被风吹得一阵明一阵暗,讲不出的凄寒。
这又是沈宗良说的,家里总是闹腾腾的灯火辉煌,叫别人见了,以为时时在夜宴宾客,拉帮结派的名声传出去不太好。
且惠就没见过在作风上这么保守谨慎的人。
何况他才三十岁,将来再长些年岁的话,岂不是要成人精了吗?
她走在唐纳言后面,穿过迂回曲折的游廊,卧室里传来几声叫唤。
且惠惊恐地瞪大了眼,唐纳言回头安慰她说:“应该是在扎针,没事儿。”
怎么可能没事?
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何况是这么重要的部位。
唐纳言敲了敲门,是隋姨开的。
她已经不忍心再看了,直直摇头说:“这回二哥儿的身子吃大亏了。”
再一扭头,看见且惠就在身后,她像见了救命恩人。
隋姨拉过她,“钟小姐,你就别走了,照顾照顾他吧,我也不方便啊。”
且惠越过唐纳言的肩膀,往里面看了一眼。
珠罗圆顶帐子下,躺了一个肩宽腿长的沈宗良,他趴在那里,看不见脸,腰上插满了银白细长的针。那些针在灯下轻轻地摇晃,让且惠的心尖肉也跟着颤动。
这得多疼啊。
她一下子就酸了眼尾,对隋姨说:“您放心,我今晚不走。”
隋姨给大夫搬了把椅子,问:“这要扎多久呢?”
大夫也不敢坐,摆手说他站着就好了,“十五分钟后我拔针。”
最后且惠坐了上去。
她从包里拿出一条丝巾来,深蓝色的,对折一下,刚好盖住额头。
且惠把手伸过去,给沈宗良擦了擦鬓角上的汗。
他本来闭了眼在休息,被这么一弄,不高兴地啧了一声。
但睁眼一看,面前坐的人是钟且惠。
她已经脱了外套,穿了件纯白的一字肩轻薄线衫,露出精致漂亮的锁骨。
沈宗良疑心他是不是扎针扎糊涂了,在做梦。
他先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再慢悠悠地环视一圈,该在的人都还在。
唐纳言上前解释了句:“我们在陈老那里吃饭,她说要来看看你。”
且惠问:“你怎么样了?还疼吗?”
沈宗良刚要说不怎么疼。
大夫先应了一声说:“那怎么可能不疼?总还要疼个七八天吧。”
听后,且惠捏着帕子,拧起两道细眉说:“那么久。”
“没关系。”沈宗良拍了拍她的手背,“我这算工伤,正好在家休养一阵子。”
且惠听着他的离谱发言。
她忍不住瞪了他一眼,“这样的假要休来干什么。”
满屋子静悄悄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人都退了出去。
也许是为了方便大夫施针,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很晃眼。
且惠在浓稠的光线里,看见沈宗良的目光安静而直白,落在她的身上。
她低了一下头,侧过身子不敢看他。
沈宗良捏着她的手,小心地问:“今天不走了吧?”
这话令且惠好笑到结巴的程度。
她反问道:“你这、你这都生活不能自理了,怎么走啊?”
“就是说啊,别人一碰我就浑身难受,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了。小惠,你不会抛下我的,对不对?”
说着,像急于得到她的回答似的,沈宗良也不管后背上的针了。
看他那个架势,还是撑着手肘坐起来。
且惠吓得小脸煞白,把他摁得牢牢的,“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从她回家过年,到闹了这么一番口舌,沈宗良很久没听她这么软绵地说话了,心里痒痒的。他喉结动了一下,“让方伯去把你的行李都拿来,好吗?”
怕他又要乱来,且惠忙点了点头,“都可以,你别再操这份心了,好好躺着吧。”
这时,外面叩了三下门,“钟小姐,我能进去吗?”
且惠说:“隋姨,您进来吧。”
很快大夫就拔了针,又开了外敷的膏药,说明天再来。
他对且惠说:“这些天要格外注意,晚上睡觉的时候......”
“肖院长,您稍微等我一下。”
且惠忽然对他喊停,大伙儿都看着她。
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珠帘跑到书桌边,拿了纸和笔。
几秒后,又再气喘吁吁地回来,“好了,说吧,我都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
床上的沈宗良听笑了,对旁边杵着的唐纳言说:“你看她,书呆子一个。”
唐纳言对他这种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行径大为不耻。他说:“书呆子你也疼得要命,今儿要不是我,你还能够有这份照顾?你就说吧,这一回怎么谢我?”
沈宗良瞄了一眼且惠,“谢什么谢!我让你不要告诉她,不知道她禁不起吓啊?”
“好好好,这还成我的错了。”唐纳言拍了拍膝盖,“走了,咱不在这儿碍眼。”
沈宗良叫住他,“等等,合同过两天会送到你办公室,已经过审了。”
这厮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就知道,我们沈总是从来不会亏待兄弟的。”
他听不下去这种话,皱了下眉,“你给我滚蛋。”
这一边,且惠写了大半页纸才勉强记完。
比如,不能劳累,不能着凉,多吃蛋白质,建议仰卧位,可以在腰下面垫个枕头缓解一下,但过段时间就得拿掉。
她送肖院长出去,“谢谢,您慢走。”
隋姨让她回房间去,“我送肖院长上车,你快进去,自己别着凉了。”
且惠走回去时,碰上唐纳言出来,他说了句,“今天得你的济了,且惠,下次还叫我送你啊,我有空的。”
她懵懵懂懂地啊了一声,“纳言哥,你在说什么呀?”
唐纳言指了指房内,“没事,你进去吧,那边脖子都伸出二里地了,就等你回去呢。”
“哦,好。”
沈宗良已经翻身坐起来,腰下垫了松软的枕头,靠在床头。
他身上穿着睡衣,想是中医院的人来之前,就洗过澡了。
这么一来,且惠也没什么可忙的。
加上彼此又冷了这些天,乍然四目相对,她还真有一点不适应。
且惠垂着脸,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
她忽然问:“你吃了晚饭吗?要不要吃一点?”
但沈宗良点头,“吃过了,不吃不好扎针。”
“哦。”
一项计划落了空,且惠又筹划起另一样,“你吃苹果吗?我给你削一个。”
他清淡地说:“又硬又酸的,不吃算了。”
她又低头沉思起来,从来没觉得聊天这么艰涩过。
等再一次抬眼,且惠说:“你要不要......”
“你安生坐着吧,我也没那么难伺候。”沈宗良当机立断地拉过她的手,一径看着她温柔地笑:“今天懂事了,不像前阵子似的,两眼一睁就是跟我怄气。”
且惠脸上一红,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没有吧。”
沈宗良疑惑地问:“嗯,你没有吗?谁把我从她家赶出来的?”
她因为紧张,手里不停迭着那条帕子,四方的,三角的,各种各样。
忽然被沈宗良抽走了,他认了认,“这看着眼熟,我的东西吧?”
且惠抢了下来,“去年国庆前你把它拿给我擦汗,现在是我的了。”
都不用去闻,那股深幽的少女体香就钻进他鼻子里。
沈宗良感慨道:“那是,都和你一个味道了,它也不认我啊。”
且惠又折了两下,随手放在床头柜上,她说:“这段时间总失眠,我拿它盖在脸上睡觉,很快就睡着了。”
她总说自己不懂恋爱,却很会在不经意间,讲出一些动人的情话。
沈宗良看着她,雪白纤细的四肢配了一副恬静的眉眼,低眉敛首也是一番风情。
他用力地吞咽了一下,拍了拍床单,“小惠,你离我太远了,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