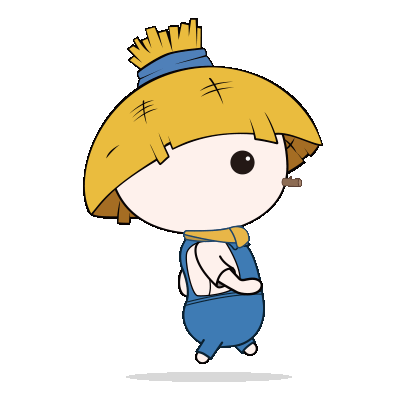老旧路灯,散发一种含含糊糊带着橙色的光。
就像裹着蚕蛹,也亮,勉强照着墙皮,却呈现一种看不透又危险的色调,还带着一股惹人胸闷的俗气。像宋方霓对青春期的感觉,也不是没有感受到温暖,但总是觉得四面八方地被束缚着。
郊外的铁建干部学院集训营。
几个高中生模样的男生正在门口聊着天,拿着冰啤酒,间或伴随着会心的笑声,却听到旁边的门吱呀一响。
一个削瘦,穿着齐膝短裤的短发女生箭般地跑出来。
路灯光圈滑出一个半圆的角度,照在宋方霓柔软的头发上,形成小光环。
一路奔到无人大道处,公路旁边的昏黄路灯下面,握着电话,宋方霓说了句“妈妈”。
参加集训半个月,每隔几天,会准时接到母亲的电话。
母亲自顾自地提高嗓门,说起家里的事情,说她父亲今天在给一个人理发时,被脾气糟糕的顾客打到鼻破血流,住进医院。
——这是假话。
老实的父亲和顾客口角几句,根本没有肢体冲突。至于闹进医院,更是无稽之谈。
从她记事开始,母亲喜欢撒谎。
不是弥天大谎,就是喜欢夸大事实。生活里一些碎屑细节,在母亲嘴里,会无比地放大乃至扭曲到戏剧色彩。
宋方霓牢牢记得小时候,妈妈突然平静地说得了绝症,以后,她就要成为孤儿。小宋方霓惊惧到每晚睡前都在床上流泪。
事后母亲坚决不承认说过这种话,转头笑着说女儿过于敏感。
“……哎呀随便学学。那么用功干什么?随便考个普通一本可以,隔壁你王阿姨,她侄子的成绩一般,都能上了x理工,敲锣打鼓地各处说。咱们如果考二本,复读一年。你不想复读没关系,帮你爸爸开店。咱们家又不是少你一口饭哈哈哈哈哈。”
耳边的母亲又说着半真半假的宽慰话。
宋方霓静静地抱着膝盖,坐在马路边。
国产手机搁在旁边,开着免提,她在路灯下听母亲殷殷切切地絮叨半个小时,间或“嗯”两声,直到母亲心满意足地结束通话。
他们的住宿部挨着清河。
一条长长的、荡漾的,但绝不清澈的河道,曾经臭名昭著,承载了好几个小区的垃圾排污任务,市政府这几年才在民声抱怨中大力整治它的水质。
蝉,依旧亢奋鸣叫,晚风,吹拂着额角的碎发。
宋方霓用手臂撑着身体,她眯着眼睛跟自己说:再坐五分钟。
她出神地凝视着黑黢黢的河水,随后顺着坡度到岸边蹲下,用指尖沾了一下河水,再凑到鼻子下面。
真臭。
河里估计没什么大鱼,她暗自想,但可能有点小鲫鱼小白条之类。
不适合作为钓点。
就在此时,黑色的夜雾里,有人远远地顺着河边的小道跑过来。姿势轻快好看,几乎是瞬间就移到面前。
男生居高临下地和蹲在河边的她对视一眼。
他显然看到了自己嗅河水的古怪动作,宋方霓下意识在短裤上蹭了蹭手心,对方抿了下嘴,目不斜视地继续夜跑。
宋方霓平静地爬到原先的绿化带坡,继续对着河水发呆。
蝉,依旧亢奋鸣叫,晚风,吹拂着额角的碎发。
又过了会,她原路返回集训住宿处。
门口处几个男学生早已经不见踪影,地面有几个空瓶子和乱扔的薯条垃圾袋,台阶上,换成一个高瘦身影,做着跑步后的拉伸肌肉动作。
擦身而过,两人没有说话的意图。
梁恒波。
也是来参加集训的本市学生。有一个看起来很土气,念起来,却有特殊韵味的名字。
他们曾经在全市高一、高二的理科竞赛上碰面几次。宋方霓就读于西中,他读的白区附中。两所都是重点高中。
这一次暑期集训,他们坐前后桌。
他每次的课桌都拉得稍微靠后,规规矩矩坐着,从来不会把腿越界到她凳子下面。
他总是戴着耳机听walkman。
他每晚有夜跑的习惯。
他是这一群男生里长相最为出挑的“头牌”。
宋方霓对梁恒波只有这么多的了解,还是晚上洗漱时,听同宿舍的女生裴琪说的。
她的头脑和精力被集训占领。
能来参加集训完全是意外,这是三校联办的竞赛强化课,十几个尖子生像被屠宰的小羊羔拉来城郊,做针对比赛的短期封闭训练。
训练营里的学生既是佼佼者也是竞争对手,谁能赢得这场竞赛的名次,也赢得本校的报送名额。
除此之外,宋方霓还要准备高三开学的模考。
数理化三科里,她数学成绩最好,物理却较为普通,怎么学都不开窍。班里的尖子生咬分都很紧,差一分可能拉开距离。物理却能让她总成绩退后20名。
宋方霓烦闷之余越发压榨自己。
集训的自习室里开着落地空调,老师翘着二郎腿坐在讲台上,等着学生拿着问题上去答疑。
宋方霓拿着试卷从讲台走回来。
半个小时后,她泄气地把手里的铅笔扔到桌面。
明明刚才已经听懂老师的点拨,回到位置,却怎么算不出这道物理题的正确答案。
宋方霓重重地靠回在椅背,揉了揉眉毛,却听到身后“嗯”了一声。
后座男生放在桌角的一瓶可乐被她的后坐力撞翻,塑料瓶滚落到椅子的夹缝里,幸而瓶盖被紧拧住,但瓶身上面凝结的水珠还是沾湿女生的衬衫。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两人异口同声地道歉,声音都很低。
对方已经站起身,借着身高优势,看到她在桌面被涂抹成黑疙瘩且满是笔洞的草稿纸。他收回目光,依旧有点无动于衷的表情。
宋方霓也在同样扶稳可乐瓶时,瞥到对方的试卷写满了答案。
她干脆地回过头,看到近处的空调上面绑着的一根粉色丝带被吹起,静谧非常。
……自己大脑里有包吧!自责着,她继续做题。
到了晚上,母亲的电话如约而来。
她依旧跑到路边接听。母亲这次诉说的话题,埋怨父亲出轨了,仅仅因为今天给客人剪发,他盯着电视里播放的沐浴液广告出了神,而广告里有金发裸女,老不正经的玩意儿。
宋方霓不搭腔。
没什么好说的,她头顶的路灯悬挂着,四周有巨大的蛾子扑过去又绕过去,重重叠叠的橙色光,现实且肮脏。
宋家是一个拆迁户。
没有外人想象中的豪气,为了选择拆迁款或补偿房,大伯家、叔叔家、姑姑家和奶奶家就打起了民诉官司,直接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宋父最后只拿了最小的两套房子。
除了收租,宋方霓父母开着一家理发店,她父亲是典型中国北方男人,疼老婆疼孩子,平时的话少得可怜,爱钓鱼,唯独喝高了,会用一知半解的知识,激烈讨论什么台湾,俄罗斯和美国问题。
宋方霓母亲则完全不含蓄,在理发店无时无刻不吸引每个人注意力,总是盈盈又大声地和每一个顾客开玩笑,很招人喜欢。她从不避讳在女儿面前,和丈夫表现出非分的亲密,甚至会搂着脖子和丈夫亲吻,也最爱和陌生人吹嘘,有一个读全市重点高中重点班的独生女。
宋方霓自小为妈妈身上的那股媚意而难为情。
她长得比母亲还漂亮,鼻高眼深,个性却极为端静、骄傲和沉默,在生人面前甚至从来不肯先开口说话。
电话里话题一变,母亲突然问宋方霓愿不愿意出国旅游。今天有一名顾客烫发,说全家去了趟新马泰,感觉不错,母亲说家里可以拿出3000块钱,供她出国玩。
宋方霓闷闷地听着,用手捡起地面的石头,投入到远方的清河河道。
从小到大,自己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深圳蛇口,参加数学比赛。家里不算揭不开锅,但不会把钱投入到旅游,更别说送女儿出国旅游。
宋方霓明知道母亲只是空许诺,内心的某一部分,隐隐渴望着母亲会转变心意,愿意去实践这一个飘渺的许诺。
总之继续努力学习。
她低头想了会,只能看到这一条微渺的道路:等,上了大学就好。
集训到了最后一周,十几岁的少年或多或少开始产生了些许浮躁。
白天上课,有些同学不再按按原座位就坐。
比较熟的,会在课间坐在一起聊天,尤其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女生,熟悉得更快,叽叽喳喳的。
宋方霓有一天早晨去晚了,发现她的原座位被另一个女生占了。
她犹豫片刻,坐在后排。
男生的课桌非常干净,桌斗里没有放任何参考书,桌面右上角,用英文花写体写了Radiohead。这应该是他喜欢的乐队名。
两分钟时间不到,原座位主人走进教室,斜背着深色的书包,一边的耳机线垂在肩膀,轻车熟路地来到这一排。
宋方霓心想是否应该解释什么,又觉得少废话了直接起身让座吧,这么瞧着梁恒波也抬起头。他停在几步之外,目光一转,看到宋方霓座位被其他女生占据。
几个爱偷偷聚在门口喝酒的男生们,出声叫梁恒波去他们那里坐。梁恒波便用目光示意她不需要动,横穿座位,走到他朋友那里。
宋方霓暗中松口气。
瞎紧张什么呢,她好笑地问自己。
不包括每次传卷子的礼貌“谢谢”,和前几天的“不好意思”,他们从来没单独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