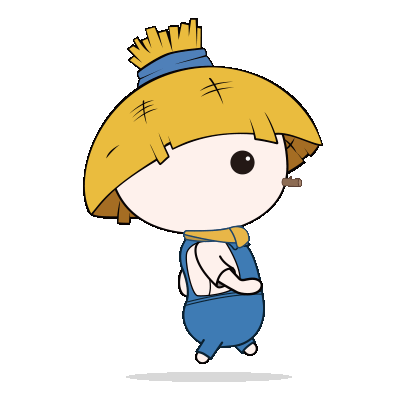第二天, 是被手机吵醒。
梁恒波的大学同学让他们赶紧滚起来,还去不去宏村了,青旅的老板娘也开始敲门催他们退房。
宋方霓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梁恒波已经从床侧站起来。
退房的时候,老板娘阴阳怪气地提起,旁边的客人投诉他们昨晚房间里的动静太大。
梁恒波站在前台处,脸整个都红了, 他按了眉毛, 说对不起。
对着那一张面孔, 老板娘很快原谅了他。
“年轻人啊。”她啧啧感慨,“体力好。”
宋方霓幸免于难。
梁恒波去还房卡时,她抱著书包, 提前低着头溜出来,远远地,就站在外面的街道口处等他。
当知道他被刁难,宋方霓的脸也红透了, 但又有点庆幸自己不在现场,捂着嘴,偷笑了半天。
梁恒波帮她背著书包。宋方霓就在旁边揉着脖子,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等舒展完了, 重新扯住他的胳膊。
一抬头,却看到男生抿着嘴, 似笑非笑地盯着她。她奇怪地说:“怎么了?”
梁恒波收回视线:“……我在想,你是不是又该饿了。”
是的, 他们还没吃早餐呢,确实饿了。
她不太好意思去承认,就随口说:“那, 你不累嘛?”
“我应该没有你累。”
触到他有些促狭的目光,宋方霓终于发窘地掐了他胳膊一下。
两人在找到同学前,彼此都没说话,目光一对视就忍不住想笑。
路上的时候,大学生们讨论买什么黄山特产。
宋方霓第一时间所想的,基本全都是吃的,什么烧饼梅干菜酥,油栗,茶糕,还可以买点当地的辣酱带给宿舍其他女生,昨天吃的松子仁也挺不错的。
但他们那些人讨论的,都是什么歙县砚台、泾县宣纸、临泉毛笔等等。她在旁边心不在焉地听。
梁恒波在一家小吃摊停下,买了包姜糖和芋头丝。
他停下的功夫,其他人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等着梁恒波。
宋方霓吃惊地接过零食,内心在甜蜜之余也很有一点害羞,就让梁恒波和朋友聊天,不用管自己。
逛宏村的时候,梁小群打来电话。
“你被卖到山里去了吧?”梁小群嗔怒,“都几天,也不给我报个平安。”
梁恒波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对不起。”
他独自缓慢地往前走。
宋方霓已经不见踪影,估计跑去哪里逛了,她并不喜欢“秀恩爱”,有一种特别独立的感觉。他想到以前辅导她做题,每次指出哪里有误,也从来不需要安慰她的情绪,她只会继续认真地投入到每一件事情里。
“这次去黄山,是去见你的那个樱桃小丸子吧。”梁小群问,“既然那么喜欢她,怎么不追她,让她当你女朋友?我一直不反对什么早恋,而且,你们现在也都读大学了。”
梁恒波没说话。
“……还是说,你已经吃定人家,吊着人家?我还就告诉你,那丫头在上海读书,未必身边就没有男生追,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梁恒波闭上眼睛,阳光照在他的眼皮和喉结上。这是朋友去世以来,他内心罕见的,觉得一种彻底轻松的时候,他深深地呼吸一口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
梁小群喋喋不休地说:“……那个小姑娘长那么漂亮,你懂的。”
“好了,别多管了。她已经答应当我的女朋友了。”梁恒波终于说。
顿了一下,手机里听到梁小群爽朗的笑声。
“你能不能不要笑得像个老巫婆。”他口气略微不耐烦地,其实也在笑。
梁恒波这时候看到,路边有人卖那种竹编的草饰,编得非常精巧。他想到,梁新民一直很喜欢这种东西,不过他笨手笨脚的,买来不久就经常会被弄坏。
口袋里还剩下最后一点钱。
“好吧,你什么时候带樱桃小丸子来见我?”梁小群问。
“她在上海上学,暑假才回来。现在见你,怕你给她压力。”他半开玩笑。
话筒那里却沉默了会。
梁小群的口气却严肃起来了:“嘿,我刚刚开玩笑,你啊,好好和人家小丫头相处,千万别告诉她你舅舅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告诉她了,一定跟她解释清楚,你舅舅,他是摔到脑子没及时治才变成现在这样的。家里还有他当时的医院病例,你舅舅真的不是一出生就痴呆了,我们家的基因绝对是健康的。我不骗人。”
“莫名其妙啊你。”他打断她,“突然讲这些干什么。”
“当然要说明白啊。咱家的条件很一般,估计女孩都嫌弃。”梁小群忧心忡忡,“你真的要对人家好一点,当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梁恒波在小径中央停下了脚步。“你说的那句,我们家的条件女孩都嫌弃,是什么意思?”他问,“我们家里怎么了?”
梁小群干脆地回答:“穷。咱家很穷。”
梁恒波站直不动。
他看着眼前的宏村。青砖黛瓦,有一种特殊的诗意,一洼池水衬着背后的水杉,远近建筑错落有致。景色静而美,没有任何污秽。
一路上,有不少画家来这里写生,穿着朴素。
他轻轻地说:“宋方霓不是那种物质的女孩子。”
“谁跟你讨论你女朋友物质不物质了,我只是说咱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家很穷。”梁小群随后转了话题,“小波你呢,就当散心,和她在黄山多玩几天。如果身上没钱,我今晚再给你点,我和你舅舅在家很自在,老实说,他看到你不在,高兴坏了。总算没人管他了。我开的服装店……”
挂了电话后,他把手机收到兜里。
经过下一个路口,梁恒波买了两个手工饰品,小贩用塑料袋装着,伸手递给他。态度很热情。
梁恒波接过来,看着对方黢黑的皮肤。
他从没摆过地摊,但是,梁小群摆过。
印象里,梁小群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卖过衣服,卖过水果,摆过地摊,当过保洁,当过保安,送过外卖,总是想方设法赚钱。
不过,她对儿子和弟弟很大方。小的时候想报任何兴趣班,或者想买什么书,梁小群二话不说掏钱。她根本都不知道Daft Punk和Sex Pistols,但是那群玩乐队的孩子暑假来家里玩效果器,她从来不说什么电费,带着梁新民躲出去。
梁恒波也知道,家里的情况是捉襟见肘,可是,他从小的成绩极好,在学校更是被老师抢夺和重点培养的对象,等稍微长大,他也凭借自己能力赚零花钱,减轻母亲负担。所以从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宋方霓也会苦恼于她家很穷。
但是,女生嘴里的“穷”,是文艺的“穷”,是和郑敏和欧阳文家相比较的“穷”,是她们家拥有两辆丰田高配车的“穷”,是宋方霓咬咬牙依旧能在大一掏出驾校费用的“穷”,是她拥有不少东西只是那些东西可能确实很土很廉价的“穷”。
她的穷,更像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克扣。而不是梁恒波所定义的。
“穷”不是“匮乏”,而是“没有”。
梁恒波从没想过,宋方霓可能看不上自己家。
这时候,裴琪跑过来。她笑着说:“恒波,买什么好玩儿的东西,让我看看。”
梁恒波沉默地打量着裴琪。
据说,裴琪那样的才算是有点钱,背着的小包是他好几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关键是,她很少背相同的包。
宋方霓会嫌弃他家穷吗?她在高中开始,就有一个极其有钱的追求者。
裴琪被梁恒波若有所思的打量弄得微微脸红,她说:“哈哈,别这么看我,小心你的女朋友吃醋啊喂。”
梁恒波回过神:“没关系,我现在正在想着她。”
裴琪的目光中闪过一丝复杂。她看着前方,两人沉默地并排往前走。
宏村湖水很静,四下了无尘意。
过了会,裴琪歪头,低低地说:“我知道,你妈妈最近没给你天天送饭了。”
梁恒波冷淡地看她一眼。
“就,关心你一下。因为,你前段时间的状态真的很不好,我也知道,是你看到……”
“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梁恒波沉下语调,“但那都是我的私人事情,和其他人没有关系。现在和方霓出来玩,我也并不想讨论这些。”
即使微微不快,男生依旧是不紧不慢的说话。
裴琪长久地侧目看着他,她戴着遮阳帽和冰袖,陪着他继续往前走。
过了会,梁恒波四下回头找宋方霓,她的人依旧没回来。
打她的电话,电话占线。
梁恒波问了裴琪,裴琪说宋方霓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后就跑远了。
这女生,每次接电话都避开人,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梁恒波给她发了几条信息,让她赶紧在自己眼前出现。等两人逛完宏村,就甩开其他人,不需要带着一堆电灯泡走。
发完信息后,梁恒波心不在焉地继续在宏村转。
过了会,手机终于响了。
电话那方却传来一阵压抑的啜泣声,宋方霓强行镇定着,要梁恒波陪她坐最近的高铁,两人马上同回北京。
>>>
妈妈昨天晚间开车进货,撞到了前方的卡车,被送进医院的急诊。
梁恒波陪着宋方霓坐高铁,她就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也没哭,也没崩溃。
他把刚才买的零食递过去,宋方霓摇摇头,但稍微再劝了一句,她也乖顺地吃了。
列车刚停稳,宋方霓就站起。
等赶回市里,来到医院,已经是晚上了。得知母亲脱离危险时,宋方霓才松口气。
车祸造成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是医生开了一个腰椎正侧位片,在平片上却发现了腹主动脉瘤。那是一种“表面健康的人送到医院,第二天可以说没就没了”的凶险疾病。
凌晨两点,宋方霓坐在椅子上,她低头看着郑敏小心翼翼地问是否有家人得了该病的短信,感觉到一股凉意。
梁恒波已经走了,他在医院里陪了她好几个小时。
父亲在旁边,用手撑着头。
宋方霓这时候才知道,她在上海上了大学,她父母觉得理发店的生意可以不用求稳。爸爸准备扩大理发店店面,抵押了家里的两套房子,又借了一笔钱,准备加盟一个连锁的理发店。
加盟费一下子收取六十多万,之后又投入了不少钱,还要选新的店面装修。
这一切在妈妈住院后戛然而止。
之后一周多,妈妈住在icu。每一天烧得是大量金钱。
爸爸始终不肯放弃,宋方霓也向学校请了假。
她终于知道,人在这种时候是不可能有任何闲心想别的。
从坐在回程的火车上,黄山瑰美的日出和难忘的初夜,就已经彻底地在脑中被抹去。
她不停地想妈妈在出事前打得最后几通电话,自己疲倦地睡过去了。第二天白天在黄山玩,她忙着吃醋,忙着恋爱,忙着各种那种小事,并没有及时打回电话。
这太可怕了。
感觉就像被书页划破手指,等有痛感的时候,已经无可挽回地收获到了一个流血的伤口。
梁恒波问过她几次情况,宋方霓也都没有回复。
她心中有一种奇怪的笃信,这也是一个命运里的jinx。
越是重要的事情,别人越是不能打探。问了,就好像是催妈妈命一样。
但是金钱始终不能留住人。
那个妩媚的理发店老板娘,爱玩夸大其辞狼来了的游戏的妈妈,在最后一次手术去世了。除了遗体,到底也没见到最后一面。
爸爸一夜白头,加盟的理发店也干不下去了。
家里其实有积蓄,但因为要加盟新生意,又加上付了icu费用,这么算下来几乎所剩无几。
车祸事故里是妈妈的全责,还需要负民事赔偿,这么算下来,家里还欠了四十多万的外债。
爸爸把新店面和家里的车都卖了,旧理发店干不下去,外聘的理发师拿了薪水走人,但不少老客在他家还有一部分储蓄卡,加在一起有七万多,也要赔退。
有暴躁的顾客直接上门,把她家的玻璃砸了,爸爸嘴笨,每天都在处理和解释这一些事情,他担心宋方霓的安全,嘱咐她去一直没联系的姑姑家借宿。
正为难的时候,郑敏热情地提出收留她。
郑敏平时都住医学院的宿舍,让宋方霓住自己家,反正她父母都是医生,经常不回来。
宋方霓提着少量的行李,呆呆地等在公交车站。
她房间里大部分都是书籍,还有高中时积攒的各种本子和笔纸,厚衣服都是冬天的,并不需要带过去。
这时候,突然有人长按喇叭。
前方开来一辆苹果绿的跑车,锃亮的车标是一匹站立的骏马,引擎发出响亮轰鸣。
车窗降了下来。
学校的期末考试还没结束,欧阳文却也提前回来,因为知道宋方霓家发生的事情。
他一路开车过来,看宋方霓家的理发厅这么狼藉,不由挑眉。
问清楚了欠债,欧阳文啧啧嘴:“付了,几十万至于砸人家玻璃么。有毛病。”
欧阳文没有攒钱的习惯,但他有几张银行卡,不算信用卡,最少的那一张储蓄卡里面的钱就远超过了这数字。
宋方霓漫不经心地看着行李箱上的塑料花纹,她不觉得欧阳文的钱和自己有关。
欧阳文忍不住说:“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过?”
她不知道。
这段时间以来,宋方霓觉得她的灵魂好像被切割成三部分,一部分还和妈妈在一起,另一部分和爸爸一起焦虑,还有一部分,留在上海,在远处,吃惊地看着眼下发生的这一切。
宋方霓想过最坏的情况,自己无法继续读大学,但每当这时候,就感觉坠入一个密不透风的沼泽里。
爸爸的意思,也是让她先回上海读书,家里的事情不用她管。她也管不了。
“什么?你真的打算回上海,不管你爸了?你家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以后在上海,倒是能住宿舍,但你让你爸住大马路边上,还是,你爸准备跟着你一起搬去上海,再当个剃头匠?”
宋方霓被说得内心整片刺痛,她稍微地低下头:“我正在想怎么解决。”
欧阳文沉默了一下,他也没有看到过宋方霓这么茫然过。
以前,在高中总是温柔安静又隐约傲气的女生,如今坐在露天车站的椅子上,整个人显得非常灰暗和瘦弱。
“嗨,我刚才是在逗你玩呢,多大点事。不值得,这点钱不值得咱们受气。”他柔声说,“你家欠钱也不多啊,又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
女生闻言抬起头。仿佛他之前是一棵树还是什么的,他只是恰好就长在她旁边,她此刻才意识到他的真实存在。
欧阳文温柔地说:“我知道你家出事了,立刻赶过来。”
她无言地看着他。
女生那一双深褐色的瞳孔,没有感激,没有惊讶,也没有被冒犯,有的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诧异。
欧阳文试探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借你家钱。你放心,可绝对不是同情你啊,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帮你的。”
“你的同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笑话。”宋方霓干脆地说。
欧阳文的胸膛起伏。
公交车进站了,女生看都没看他一眼,她提着自己沉重也是唯一的行李,迅速地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