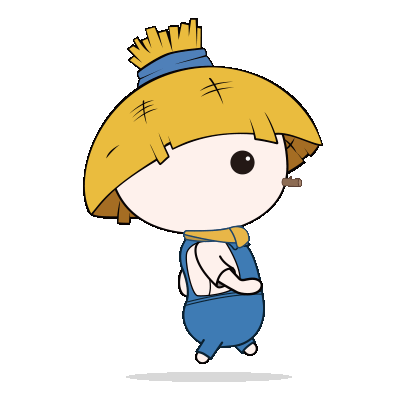今日李善等人出宫围猎, 孩子们离开后,紫桂宫仿佛空了一半。午时,皇帝和天后听说太子和公主们回来了, 只不过在马球场比赛。皇帝一听来了兴致, 和天后一起到马球场围观。
他们大概是比赛过半的时候来的, 皇帝没让人通报, 悄悄带着天后上了看台。皇帝一边看, 一边和天后点评:“裴家果真教子有方,裴纪安在场上处处照顾李常乐, 球技马术也不错,是个将相之才。”
天后同样很满意裴纪安的表现,准女婿对自己女儿深情不二, 哪个丈母娘看了不高兴?李常乐是他们从小捧到大的明珠, 放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天后最牵挂的事就是给李常乐找个好夫家,好保护李常乐一世无忧。李常乐什么都不需要付出,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开开心心长大,然后让另一个男人接过父母兄长的任务,继续宠她。
皇帝是男子, 注意力很快被比赛吸引走, 津津有味地看着众年轻郎君打马球。天后看了一会,留意到一个异常。
李朝歌为什么在后面?李朝歌被隐士高人收养长大, 按道理, 她的骑射应该远超于洛阳这些贵族少男少女才是。她为什么不抢马球,而是每次都往偏僻的角度冲呢?
她想做什么?
天后又看了一会,发现李朝歌基本围着裴纪安走, 而另一个穿白衣的男子,总是跟在裴纪安几步远的地方。不知为何,他们两人抢球时常撞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双双掉队,谁都没法去抢球。
天后最开始以为这是战术,李怀队里出一个最弱的,没皮没脸拖住对方最强的,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大展身手。但是天后看了一会,觉得不像。
按李朝歌的水平,绝不至于被人用田忌赛马这等战术拖住。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但每次都无法挣脱,就有点门道了。
天后唤来宫女,问:“那位穿白衣服的男子是谁?”
场中只有两人穿白衣,一个是李朝歌,另一个是顾明恪。宫女很快回来,恭声道:“是裴家的表公子,顾明恪。”
天后瞳孔微微放大,颇为意外。这个熟悉的名字终于把沉迷看球的皇帝拉回来了,皇帝凝眉想了一会,终于回忆起来:“是昨夜和朝歌说话的那个男子!”
“没错,是他。”天后仔细盯着顾明恪的脸,恍然道,“难怪。”
长成这个样子,难怪李朝歌一见倾心。皇帝也看清顾明恪的脸了,他摸了摸下巴,沉默片刻,道:“还真挺好看的。”
李朝歌说顾明恪长相气质远超裴纪安,皇帝嗤之以鼻,但是今天,他发现是真的。
确实,好看的不止一星半点。
皇帝本来对顾明恪印象不佳,才见了一面就能让李朝歌顶撞他这个父亲,皇帝很难对顾明恪产生好感。不过现在看了真人,皇帝偏见消散很多,真正升起了见一见此人的兴致。
长得好看的人天生占优势,自从皇帝发现顾明恪后,之后半场皇帝总是忍不住将视线落在顾明恪身上。不看还好,这一看皇帝更加意外。裴家人都说顾明恪先天体弱,不善弓马,然而依皇帝看,分明很好。
李朝歌的力气皇帝是亲眼见识过的,足足能推走野熊。现在顾明恪和李朝歌过招,看招式似乎不占上风,但是从无失手,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拦住李朝歌。
有意思,皇帝升起兴趣了,问:“裴纪安不是说他的表兄体弱多病,不善武艺么?”
天后含笑,缓缓说:“百闻不如一见,到底如何,一会叫上来看吧。”
最后一场李常乐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放水中赢球,她高兴的眉飞色舞,皇帝坐在看台上,和天后感慨:“阿乐还和小时候一样,做什么都要头一份。要是有人和她一样,或者有人超过了她,她就气得不吃饭,扑簌扑簌眼泪。”
天后其实不太喜欢这种性格,太娇气了,人生在世怎么能事事如意,只赢得起却输不起,迟早都要栽大跟头。但这是自己的小女儿,天后一边觉得不好,一边又舍不得让女儿吃苦头:“有好胜心是好事,但是她太爱娇了,日后恐会受累。”
皇帝不以为意:“她是朕的公主,大唐最宝贵的明珠,娇气些怎么了?所有人就是该捧着她,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该归阿乐。”
天后本能觉得不好,然而父母爱幺儿,连天后也不能例外。长子长女狠得下心教训,但是放到最小的孩子身上,那就百般舍不得。李常乐是天后最小的孩子,还是个女儿,天后嘴上说得再狠,心里也从不舍得让娇娇女受挫。
天后最终无奈地叹了一声,说:“罢了,她是公主,日后总不会有人踩在她头上,娇气就娇气些吧。对了,陛下,如今朝歌回来了,你方才那些话私下说说便罢了,当着朝歌的面可万万不能提。”
“朕知道。”皇帝就算不及天后圆滑,但也当了二十多年的皇帝,处事手段并不差。他还不至于这般没头脑,在李朝歌面前说最爱李常乐。
为上位者,就算心是骗的,表面上也要端平。
马球已经打完,没多久,李善等人就上来了。远远的,李常乐的声音就传入楼梯,还不等皇帝天后准备好,一个蓝色的身影便风风火火撞到皇帝怀里:“阿父,阿娘,我刚才赢了,你们看到了吗?”
皇帝被李常乐狠狠撞了一下,皇帝身体不好,经不得大动作,两边的侍从都瞬间露出焦急之色。皇帝接住李常乐,暗暗对两边人摆手,依然笑着看向怀里的小女儿:“朕自然看到了。朕的阿乐真厉害,场上这么多男儿,无一人能胜过你。”
李常乐扬起下巴,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她还穿着男子服饰,此刻窝在皇帝怀里,颇有些不伦不类,唯有一张小脸白皙光滑,一看就知在家里十分得宠。李朝歌跟在李善、李怀身后,慢慢走上来,规规矩矩给皇帝、天后行礼:“儿参见圣人,参见天后。”
“快起吧。”天后笑着对李朝歌招手,说,“朝歌,坐到我这边来。”
天后有意摆平李朝歌、李常乐二人的位置,然而宠爱是藏不住的,两个公主哪个更受宠,实在一目了然。李朝歌明白父母更喜欢李常乐,也明白天后是好意。但是她当真不习惯和人靠太近,坐在天后身边,简直身上每一根汗毛都在难受。
皇帝不及女子心思细,并没有注意到两个女儿的细微变化。他看着两个女儿一左一右坐在身侧,两个儿子站在堂下,不远处是准女婿,几个孩子俱如青松修竹,聪慧灵巧。皇帝长叹一声,觉得人生至此,已再无憾事。他捏了捏李常乐的鼻子,道:“你瞧瞧你,穿着郎君的衣服,却还窝在耶娘怀里,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哪有公主的样子?若是让外人瞧见,岂不笑你?”
“这里又没有外人。”李常乐拍开皇帝的手,恼怒地瞪了皇帝一眼,“阿父,你都捏疼我了!”
“就你娇贵,说你一两句你还不乐意。”皇帝道,“你看你姐姐,多稳重大方。你啊,是时候脱离小孩子心性,学着当个大人了。”
皇帝话中提到了李朝歌,李常乐笑容微敛,抬眸看向李朝歌。李朝歌跽坐于双腿之上,身姿端正笔直,眼睛半垂着,睫毛在脸上晕出细碎的阴影。看起来,确实极有帝国公主的风范。
李常乐瞥到自己身上宽松素淡的男装,顿时觉得浑身不对劲。曾经新奇无比的衣服仿佛长了刺,让她坐立不安。
李常乐赢球的好心情瞬间一扫而光。她今天一整天都这么丑,还在马球场上荡的灰头土脸,而李朝歌却穿着精巧漂亮的胡服,浑身一尘不染,有李常乐作对比,李朝歌可不是大出风头。
李常乐无比后悔今天穿了男装,她应该也穿胡服的。李常乐情绪迅速低落下去,变化十分明显。皇帝看到,惊讶问:“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
“没什么。”李常乐闷闷不乐,瓮声道,“我不想长大,只想永远当阿父阿娘的小孩子。”
皇帝听到,又无奈又好笑:“你啊!人都要长大,怎么能永远当孩子呢?”
“我不。”李常乐用力抱住皇帝,噘着嘴道,“我就不长大,我就要永远赖着阿父。”
李常乐是幼女,最黏父亲,而皇帝也最疼李常乐,对李常乐的偏心根本掩饰不住。天后扫过其余几个孩子,道:“你们几个无论长多大,在父母跟前,永远都是孩子。太子是储君,日后要支撑朝廷,应当稳重,但朝歌你也是父母的掌中珠,不必这么拘束,安心当个小孩子就好。”
李朝歌顿了一下,她不想扫兴,但是,她并不想被人当做小孩子。
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五六岁不谙世事是可爱,十来岁不谙世事是天真,十五六还没头没脑一心当自己是个宝宝,那就是蠢了。相比于可爱,李朝歌更喜欢听别人称赞她聪明、美丽、强大。
幸好这时候一个内侍进来,解了李朝歌的围。内侍给皇帝、天后行礼,垂首道:“圣人,天后,顾郎君到了。”
这是天后派人去请的,天后立即说:“宣他进来吧。”
听到有人进来,李常乐终于收敛了些,从皇帝身边坐正。内侍引着一个人进来,随着他走上台阶,仿佛一阵朦胧的光从天边传来,整个看台都被照亮了。顾明恪长袖自然下垂,他双手微合,不卑不亢给皇帝和天后行礼:“参见圣人、天后。”
他说话后,整个看台都静了静。李常乐近距离看着顾明恪,一时呼吸都停了。李朝歌本来无所事事,等顾明恪进来,她的眼睛顿时有了落处。李朝歌看着顾明恪优秀的眉骨,挺直的鼻梁,清冷的侧脸,再一次感叹美人就该被优待。
仅是这张脸,看着就让人心生愉悦。皇帝和天后也被这样的美貌杀到了,过了一会,天后最先反应过来,笑道:“原来你就是顾明恪,快请起吧。”
“谢天后。”顾明恪行礼后,垂袖站在一边。他身姿舒展,修长笔挺,长袖压在衣服上,衣摆又自然堆及在地。清风吹过,他身姿不动,唯有衣角轻轻摇晃,宛如雪落清辉,千山月明,好看的仿佛梦境。
皇帝一家都是颜控,皇帝马上对顾明恪印象大好,连说话语气都不知不觉温柔了:“你便是顾尚的独孙,顾家唯一的后人,顾明恪?”
顾明恪微微颔首:“是在下。”
天后笑着接话:“顾公乃国之栋梁,我拜读北朝史良久,越读越钦佩顾公之渊博明理。能见到顾公的后人,实乃我之幸运。”
“天后谬赞,愧不敢当。”
“顾公著史是功盖千秋、惠及后代的盛举,受再多赞誉都是应该,有什么当不得?”天后视线扫过顾明恪,柔和问,“听裴大郎君说,如今你已经在修撰隋史后篇了?”
这是原本的顾明恪修的,并不是他。但秦恪如今用的是顾明恪的身份,倒也不担心顶替别人的功劳,于是他微微垂首,说:“不敢称修撰,不过略通一二,斗胆完成先祖遗愿罢了。”
天后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史书,她即兴问了几段北朝史,发现顾明恪对答如流,完全不是他口中的“略通一二”而已。天后愈发满意,对众人说:“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才学,不愧是顾家之后,不坠其祖其父威名。你今年多大?”
顾明恪心里叹了口气,表面上依然平静坦然,道:“上月初满十八。”
“十八。”天后听到这个年纪眼神微动,露出思索之色,“只比裴纪安大一岁。你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十八岁便有如此积淀,委实难得。”
顾明恪听别人称赞他年轻,实在很尴尬。但是任务在身,他又不得不把这个年轻病弱的才子人设继续扮演下去:“天后过誉。我平日并无定例,经史,杂文,律疏,都看一些。杂而不精,让天后见笑了。”
李朝歌听了挑眉,杂而不精?随便看看?李朝歌最受不了这种强行谦虚的人,于是对天后说:“天后,他的话只能信前半部分。他随口便能引用律文,他若是都对律疏不精通,那天底下就没有精通的人了。”
“是吗?”这下皇帝和天后都来了兴致。如今儒学盛行,再加上礼法话语权都集中在世家手里,洛阳里懂四书五经的郎君多,但是懂律疏的,少之又少。天后问:“你竟然懂疏义?你会多少?”
顾明恪实事求是地说:“略微了解过,不算精通。”
李朝歌一听这话又想翻白眼:“顾郎君,自谦也有个度。你这叫不算精通?”
顾明恪抬眸看向李朝歌,静静道:“承蒙公主看得起,但在下对唐律当真只是粗通皮毛,略有了解。”
顾明恪这话并没有说错,他在天界主管刑律,千年来未出一次差错。相比于他的老本行,他对人间的永徽律,真的只是略有了解。
天后和皇帝颇有些刮目相待的意思,他们最开始以为这个人只是长得好,没想到除长相外,他的才学、武功、谈吐样样不差,更难得的是,他还通识律法。
天后一力推行科举,想打破汉魏以来门阀世家垄断朝堂的局面,真正让全天下的人才为己用。其中科举,便是天后最重视的举措。她几次建议皇帝扩大科举选士的规模,除了明经、秀才、进士外,她还增设了武举、明法、明算等科目,想选拔专门的武功、律政、算术人才。只可惜并不被人重视,如今朝中官员依然以世家推举为主,靠科举考上来的,寥寥无几。
天后试探着问了几句,发现顾明恪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完全不像是自学成才的少年郎,反而像是经年的老手一般。天后大为惊喜,立刻对顾明恪说:“难得你有这般天赋,大理寺常年缺人,你这等才华不去大理寺,委实埋没了。顾郎君,你有没有想法,去试试礼部的明法科?”
明法科是专门考律法的,冷门中的冷门,每年报名的人屈指可数,而能考过的,就更是凤毛麟角。
裴纪安皱眉,担忧地望向顾明恪,想示意顾明恪拒绝,又怕太明显被天后发现。和天后走太近绝不是好事,而且,天后推荐人去考明法科,本身就是毁人前程。
以裴家的名望和人脉,顾明恪完全可以推举做官,为什么要像寒门子弟一样参加科举,岂不是叫人笑话?就算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而去科考,也该报正统的明经、进士,不伦不类的明法科算怎么回事?
裴纪安暗暗焦急,李朝歌听到“大理寺”这三个字,表情也不对劲了。她看看一脸期待的天后,又看看似乎在考虑的顾明恪,颇想告诉顾明恪别去。
她对科举没什么意见,靠考试升官发财,这是能耐。而且别看现在科举不上不下地位尴尬,等再过几年,朝堂就是进士的天下了。
世家独揽朝纲的时代终将过去,未来,属于广大的平民百姓。顾明恪参加科举可以,参加明法科也可以,但是,不能去大理寺!
李朝歌前世四面楚歌,树敌无数,但是她最看不惯的,当数大理寺。镇妖司捉妖邪,而大理寺断讼狱,看似泾渭分明互不相干,实则,两家职权重合的厉害,抢案子抢的尤其凶。
毕竟一个命案发生的时候,谁知道这是人命凶杀,还是妖邪所为?而且,不光涉及断案,刑狱权,提审权,定案权,方方面面都是冲突。一山不容二虎,显然,朝堂中只会有一家说了算。
要么镇妖司,要么大理寺。上辈子李朝歌为了和大理寺那帮老古板抢话语权,没少对大理寺下黑手,自然,李朝歌递上去的案子,也有许多被大理寺推翻。新仇旧恨太多,导致李朝歌一听到大理寺的名字就犯恶心,如今重来一世,李朝歌正摩拳擦掌等着出气,顾明恪去大理寺……不好吧?
天后微笑着等待顾明恪的答案,裴纪安紧紧盯着他,李朝歌也屏息凝神。顾明恪想了想,他虽然觉得在人间还干老本行有些无聊,但是辅助贪狼的任务显而易见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给自己找点事做,好歹能打发时间。
顾明恪很快拿定主意,他在众人各怀心思的视线中,轻轻颔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