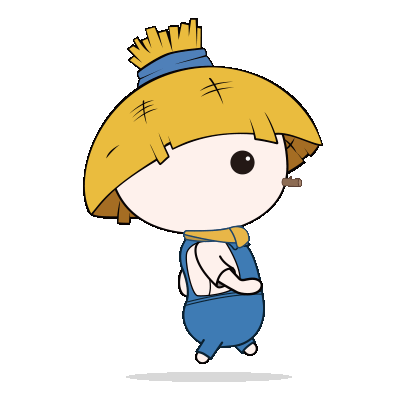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何时出发?”不知是不是被这些孜孜不倦的人整日拜访弄烦了,元崧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越快越好。”
谢长柳没有想到元崧会这么快就答应了,他以为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思量。
见他已经答复,谢长柳便不多再滞留,让元崧准备好了行囊,便带着他往回赶。
临行前,谢长柳对于元崧的出行作了解释。
“还请公子孤身一人与我前去,个中原因不方便讲述,请公子谅解。但公子放心,公子安危,我谢长柳一力承担。”
元崧善解人意,也不为难。
“我知,是去见太子吧。”
谢长柳没有说话,但不言而喻。
元崧交代好一切事由,对外,挂了出城巡视的理由,便跟着谢长柳出发。
夏日阳光如火燎,树上的蝉都被晒得有气无力。
元崧坐在车内,时不时的就要喝上一口清水缓解燥热。
“谢公子,外头日晒,你坐进来点吧。”元崧撩起帘子,外头车辕上谢长柳坐着,戴着一顶斗笠,赶着马车。
“没事。”他们此行未带任何人,就独元崧跟自己走,是以,赶车的担子就落到了他身上。
热也就热点,等太阳下山,走了林中的小道,就凉快多了。
元崧见此,感叹谢长柳的忠心不二,择君之事,一勇而成
“谢公子,太子何德何能,值得你如此付出呢?”
太子门下的印象堂里,都是他的忠臣良将,汇集各路英豪,世家子弟,忠心耿耿,然也有谢长柳这样的一笑泯恩仇的少年郎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他不该说是秦煦何德何能,而是该叹,秦煦高尚,用人不疑,用者皆善!
然而,谢长柳接下来的理由,却是教他心神震荡。
“太子,那就是此刻谢某头上顶着的太阳。他虽夏日炽热,却也能消褪寒日里的霜冷!让我的人生里,除了本来的黑夜还有青天白日!乾坤朗朗!”
是啊,有一位明君,便是天下人的青天白日,乾坤朗朗,这不光是谢长柳的太阳,亦是天下人的太阳。
若择秦煦为明君,大梁盛世可开!
太阳落土的时候,方得小憩片刻,马儿也需要吃草喝水。
他们下了车在路边歇下,谢长柳特意去搬了块整齐的石头来给元崧坐。
元崧谢过,便从怀里掏了东西出来。
他看到元崧拿出帕子垫在石头上,然后才放心坐下去。
谢长柳倒不觉得有什么,想当年在东宫,外出一应都是习惯的寝具都要搬上,连坐垫都走哪带哪。只是后来这些年,总得先活下去,哪里还有这么多讲究,席地而坐都是轻的。
他注意到素白的帕子上绣着一束谢长柳没有见过的花,蓝紫色,似喇叭状却外翻下垂。
“这是什么花?”
“鸢尾。”
听及名称,谢长柳却是了解了。
“我见过它的叶丛,倒是不知道盛开的花这么美。”
常年在外,他见过不少的河道、小路边有鸢尾丛,却因为时节不对,每每都没见过盛开的模样。
“我来的时候,正值开花的花期。”
见能与谢长柳说到一处,便同他细说,难得有共通之处。
“鸢尾有天山鸢尾、长葶鸢尾、高原鸢尾多种属系;四五月份正是开花遍野的时候,却较短,有时候趁着时间来,便能一睹风采。”
“离川城外,有一处好地方,漫山遍野都是鸢尾,常年得到河水的浇灌,每到花开的时节,繁花似锦。”
“更值得一提的是,鸢尾代表情爱、友谊、自由。”
这是谢长柳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一朵花还有这么多讲究,一朵简简单单的花却也能代表这么多东西。
情爱、自由、友谊……
如此看来,鸢尾的确值得被人熟知与喜爱。
“谢公子喜欢这花吗?若是哪日遇到喜欢的人,可以同他说说鸢尾的故事,他必定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谢长柳不说话,但嘴角却按耐不住的上扬,眼睛里都是藏不住的喜悦。
“谢过元公子点拨了。”
听谢长柳如此一说,元崧好奇心上来。
“哦?难道谢公子已经有心仪之人?”
“是有的。”谢长柳也不隐瞒,大方承认了。如遇爱人,自是不会藏着掖着,而是光明正大。
“噢?是汴京人士吗?能被谢公子钟意,一定是个不可多得的良人。”
“嗯,是吧。”会是良人吧?谢长柳也不知道,但就此时来看,情谊永恒,同心同德。
“若是谢公子不计较,哪日倒叫我见见才好。”
他志不在情爱,却也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乐见其成,更何况是谢长柳这样的良人,若是他有姊妹,也必是愿意许配给他为妻,只可惜了,他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好,快见到了。”
后来路上,元崧时而与他说说话,解这夏日的困乏。但不外乎会提及东宫,他似乎很好奇东宫,总是话里话外的想了解到东宫。
他虽是与东宫太子有族亲关系,却因元艻的关系,并不熟稔,多是会在场面上有交集,但他也知道,秦煦是个堂堂正正的天之骄子,立为东宫,当仁不让。
“谢公子,你做这一切,不是只为令尊的遗志吧?”
“我看得出,谢公子很是在乎东宫,你是很想我承志东宫门下,为太子效力。”
他心思玲珑剔透,只消几语就能猜透他人心思。
只是,谢长柳与秦煦之间,也并不清明,隔着家仇却也能不计前嫌,一心辅君。但,他看的出来,谢长柳心中是有恨的。在外流离多年,复重回东宫,一为家仇、二为君恩。
“谢公子当年是为东宫伴读,固然后来出了那些事,也没有改变你决心主事,谢公子才是大义。”
外面传来谢长柳的声音。“我若是说各为其主,元公子会信吗?”
“太子是为嫡长子,德行兼备,有勇有谋,深明大义,这样的人当值得我摒弃前嫌,投身报效。”
谢长柳坦荡,倒叫元崧不好再说。
“嗯。”
“谢公子不若再参科举?”
“元公子怕是忘了,我是戴罪之身。”
他如何不想光明正大的入仕报效朝廷,替秦煦开路,然当年旧事还未翻案,至今谢氏都是罪臣,他哪里还能科考入仕。
“抱歉。”元崧一时糊涂,想岔了,反应过来时,话已经说得出去了,心中滋生出悔意来。话茬子一开起来,就没有及时想起当年的事已经累及他的身份,罪臣,未被下狱已然是太子庇护了,哪里还能有再进科举的机会。
“元公子,这句抱歉,你说了三次了。”谢长柳不在乎这些,再刺激的话他都听过了,早已经不会为了这些小事而耿耿于怀。元崧这个人,聪慧识大体,有时候是格外小心翼翼了。
然而他是不介意,可自以为说错了话的元崧,却是自觉有憾。
“元氏之罪,人神共愤,身为元氏人,奈何吾人微言轻,未能及力,深感惭愧。”
“应诺之言,此生不悔,愿投效东宫,以匡正义,还君之情,承君之恩,望君成全。”
起初,为防让人觉得他是挟恩相报,他并不要求元崧一定答应他的提议,可奈何他的深明大义叫元崧无法再不为君所想。
“元公子言重了,元公子晓事理,明大义,而我以事相挟,惭之有愧。”
两人一来二去的,倒不会觉得各自专营心机,反而是志同道合。
“呵呵,谢公子若不弃崧,今日以山为证,结为金兰契友,日后共扶共进。”
“当得!”
难得元崧看得起他,愿以他为友,如此厚爱,承蒙不弃。
“如此便好,我字灵节,若谢公子不弃,日后你我与字相称。”
“好,只我未提字,灵节唤我长柳就是!”
两人不过几日的相处,却惺惺相惜,有志共存,志同道合,结为契友,理当如此!
一阵阵笑声自马道上传出来,响彻了幽谷逸林。
待抵达庆河城,谢长柳就迫不及待的跑去见人。
“太子呢?”
谢长柳连口水都未喝上一口就赶紧的来见秦煦,在门口看到了侍立的苏哲便问。
“在呢。”
谢长柳推门进去,又带上了门,屋内独秦煦一人,他开门进来,听到动静也没有反应,但他走进去后,秦煦却知道是他。
“回来了。”
谢长柳走上去,站在案前,看着秦煦。这甫一见到人,才恍觉,思念如潮。他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想他。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秦煦是他头顶的太阳,他那一路都在追赶他的太阳。
“是,回来了。”
他说完,气氛又宁静下来,谢长柳发现秦煦没什么兴致,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爷?”
他唤了一声,奈何秦煦依旧充耳不闻。这下谢长柳是知道了,他是生他气呢。
“爷可是气长柳不告而别?”
“这都多久了,爷还未能消气?”
“长柳与您道歉吧。”说完,他对着秦煦端端正正的行了个大礼,一如当年,他八岁时第一次入东宫,见到太子,行的那次大礼。
可他刚站直腰,秦煦好歹是出声了。只语气里,满是无奈与疏离。
“谢长柳,你总是这样。”
“我是拿你没法了。”
谢长柳对上秦煦冷漠的眼神,这一刻,他终于慌了。
“爷?”
“你别这样……”他小跑到他身边,拉着他的衣袖,满目哀求。
“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听你的,你能不能原谅我?”
瞧着谢长柳那委屈可怜的模样,秦煦又一次心软了。
“阿柳。”秦煦捏住他的下
巴,语气轻柔得不像话。
听,他又这样唤自己了,可是,他知道,秦煦不是在念旧。
“没有以后了。”这是秦煦对他下的最后通牒,谢长柳也知道,一旦秦煦认真起来,就真的没有下一次了。
“嗯,没有了。”
他答应点很快,都把秦煦气笑了。一如每一次闯完祸的他,答应下次不再犯是一样的。
待元崧浴洗过,便去书房见了秦煦。
时隔多年,本是兄弟的两人却是因为家族隔阂与山川相隔第一次难得再见。
“元大人。”秦煦看着元崧,对于这位为民生请命,不辞辛劳的的地方官本该好心情的,毕竟对彼此的声名都早有耳闻。但,由于谢长柳的缘故,秦煦还真对元崧一时好不起来,就算是元崧行礼,他都大方受了。
“微臣元崧,叩见太子,太子千岁!”元崧正正自己的衣冠,朝秦煦行礼,待受完礼,才喊人起。
“元大人请起。”
秦煦微微左倾,靠着桌边,手里拨弄着茶盖。
“元大人可知,孤传你来是为何?”
“还请太子赐教。”
秦煦松开茶盖,发出“叮——”点一声响。
“华章。”
华章应声而来,把手里的托盘摆在元崧旁的桌案上。
“元大人,请过目。”
“这是?”元崧看着托盘里整整齐齐码着钱币,有些不解。
“元大人可看出什么?”
“铜钱?有什么问题?”元崧多次观察入微,但都未能看出端臾。
“左为旧币,右为新币,新币却同旧币有出入,其外形一般无二,但量重却相差甚远。”
“元大人可知,最近一次的铸币依旧是匠造司铸化的吗?”
元崧此刻才明白,这一趟来是为何事,秦煦提及此事,关系重大,固然他只是离川一小小府尹,却也责无旁贷。
他在离川这三年,安心做好分内之事,对于他事,知道的并不多。
“这自然是……然匠造司是不可能有错的。太子是怀疑?何通?”
何通,元艻妻族,也就是元崧的舅舅。济州啊,六郡最好的地方,给了他,若是何通做好分内之事,可保一世荣华富贵。
但铸币出现了问题,只能是他那边的原因了,匠造司在他手里,朝廷颁发的铸币令也是到的他手里批阅承接的,桩桩件件,他都脱不了干系。
“微臣明白,太子是疑心元氏吧。”
秦煦不语,但也已经很明显了,不怀疑元氏就没有可怀疑的对象了。
何通是替谁办事,头顶上的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元艻在朝廷如日中天,结党营私,地方官员谋私,如今连钱币都钻营上了,以前可以既往不咎,单属这六郡之事,就足以革职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