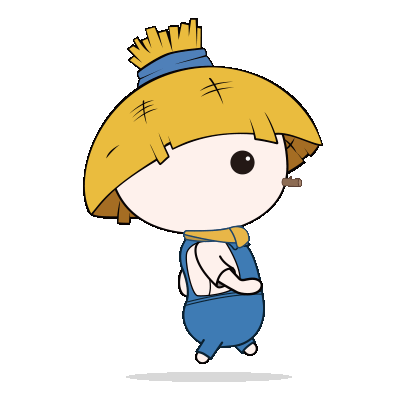傅凌傅二爷性子最是乖张,平日放浪形骸。
常把什么女子最是世间尤物放在嘴里,不是吃女子嘴上的胭脂,就是常和一些狐朋狗友去红烟阁喝酒寻乐找妓子。
气得傅侯爷禁了他的足,罚抄写佛经修身养性,望他能收敛秉性好好读书。
争取来年考个功名,就算考不上什么功名,至少也别丢了祖宗的脸。
一进屋,颀长的身躯慵懒靠在黄花梨木摇椅上,修长双腿交叠,玉带松松垮垮系在腰间。
素色锦袍被阳光渡上了一层光晕,往上,一本妙法莲花经挡住了俊逸风流的五官。
摇椅轻轻前后晃动着,显得他随性洒脱。
“大白日的爷怎么又睡下了。”吴嬷嬷蹙眉不悦道:“定是外面那些小蹄子们夜里只顾吃酒玩乐没顾好爷!”
“嬷嬷太小题大做,她们还小,再者,她们本就呆笨,您每次都这般凶神恶煞,再把她们吓痴了。”声音从经书后闷闷传出。
吴嬷嬷顿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说瑾瑶带来了。
一听,傅凌忙将佛经从脸上揭下丢到一旁坐了起来,他笑吟吟地看着瑾瑶,对吴嬷嬷挥挥手,“嬷嬷先去吧。”
二爷平日风流成性,和府中丫鬟调情在府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调情归调情,却从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故此吴嬷嬷也没觉得二人有什么不妥,便问:“那二爷打算让她做什么?是做外面的杂事还是去做分管?”
“做我的近侍就好。”
待吴嬷嬷走后,傅凌将瑾瑶拉到膝上,摇椅微微晃动着,瑾瑶只得双手抵在他胸前才勉强没压到他怀里。
看着她红晕了面颊,傅凌才心情大好地附在她耳畔问:“方来的路上,吴嬷嬷可有为难你?”
瑾瑶微微摇头。
此时庭中的几名丫鬟都趴在窗边,悄摸地往里看,奈何窗牖关得严,门也紧紧关着,只能看到二人依偎在一起的身影。
“这婢子到底哪里来的?!”夏芝瞪大了眼,“你们看到了没,二爷竟把她抱在怀里!”
一旁春蓝掩嘴嗤嗤笑着打趣道:“你急什么,二爷不也常抱你。”
“那能一样吗?咱们是家生奴,自小服侍二爷,她算个什么东西!”
身侧也有丫鬟不满附和,“对啊,咱们自小在二爷身边,她来路不明,眼下二爷正弱冠之年,血气方刚的年纪,倘或这婢子用了什么下作手段做了通房,岂不要骑到咱们脖子上。”
春蓝冷嗤,“也别一个个愤愤不平了,家生不家生的,不都是奴才,还能成主子不成?”
正说着屋内传来傅凌的声音,“夏芝。”
夏芝忙进了屋,瑾瑶已经规规矩矩站在一旁,傅凌躺在摇椅上,慵懒地命道:“把前阵子让你收着的那支镶着红翡的桃花簪拿来。”
拿来后,忽又听傅凌道:“瑾瑶簪上,给我瞧瞧。”
夏芝面色微变,捏着桃花簪的手指用力到泛白,“二,二爷,这簪子不是说,夫人让收着,日后要送给哪家心仪的贵女吗?”
傅凌掀起眼睑,眯眼睨着她,片刻一笑,拿了过来,走到瑾瑶面前,一面为其簪着簪子,一面道:“我何时说过?许是那时喝多了随意说说罢了。”
瑾瑶垂眸,面上娇羞心下却咬牙切齿,这个该死的傅凌!给赏赐不私下给,这下不给她树敌吗?!
待簪好后,傅凌捧起那张娇小的脸,端详片刻笑道:“不错,很适合你。”
这若是直接收了,那夏芝还不恨死她?刚进府她只想安安稳稳多搞些银子,可不想到处树敌!
“这么贵的赏赐,瑾瑶还什么都没做,恐担当不起。”说着瑾瑶伸手要摘下。
蓦地抬到半空的手腕被遏制住,傅凌那双狭长的桃花眼里涌上了几分不容置喙,“戴着,没有我的准许不许摘。”
这幅模样,不知为何让瑾瑶霎时想起了寺庙的那个男人——傅世子。
比以往昨夜多了丝强硬,温柔里多了份危险。
深宅又夜半。
夏芝为傅凌铺好衾被,正要为其更衣,却叫他不着痕迹的避开。
“叫瑾瑶来。”
半空的手微顿,夏芝面色僵了僵,不甘道:“二爷自幼是我服侍,那瑾瑶从外面买来的一个野丫头,哪里服侍好您?笨手笨脚的会……”
“叫你去你就去。”傅凌冷冷打断了她,见她垂眸眼眶中隐有泪光,又一笑哄道:“我知你想什么,她一个刚来的丫头,哪里威胁得到你,爷当然还是最疼你。”
对哄女人这一块,二爷到底是万花丛中过,最知女子要什么,这话正中夏芝心头烦闷,这才破涕而笑去喊了瑾瑶。
晚风徐徐从窗牖钻进,皎洁月色映得来人愈发娇俏可人。
傅凌张开双臂命道:“过来。”
瑾瑶听从为其更衣,将换了衣裳,腰部一紧就被人代入怀中,他嗓音暗哑轻声询问,“做近侍在我屋里住就行,外间的小榻是给你的。”
她侧目看去,那里是有张小榻,铺盖的整齐,显然之前这里有人住过。
她立刻想到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当是夏芝。
他既要求,她自没有不从的道理。
只是夜里她睡得并不安稳,小榻只离傅凌所在的床榻几步远,她将要睡去,傅凌就像故意捉弄她那般,要么说渴了,要么说饿了,要么说冷了,要么说头痛。
不是让她给上来暖床,就是让她给按头解乏。
以至于次日她醒来时傅凌早已离去。
刚穿好衣裳,夏芝就来了,将一摞宣纸重重放置桌上,“这些都是老爷让二爷写的,既二爷让你服侍,那这活就由你也一并负责。”
傅老爷罚傅凌抄写经文,叛经离道的人哪里肯,经文都是房里丫鬟给抄,眼下瑾瑶来了,这活自然就是她的了。
她心里那个恨,昨夜折腾的她寅时才睡,今日还要她代写经文!
一本妙法莲花经共八万余字,不能写太快,还需模仿傅凌的笔迹,从晨曦到黄昏,写得她手都麻了才堪堪抄了五万多字。
傅凌回来时,她已累得伏案睡了过去,昏黄摇曳的烛光之下,她睡得沉,以至于没发觉身侧站了个人。
骨节分明的手撩开她垂下的发丝,傅凌心情舒畅,唇角勾起一抹笑意,眼下一撇却看到她颈部的伤痕,剑眉微蹙。
这丫头……
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