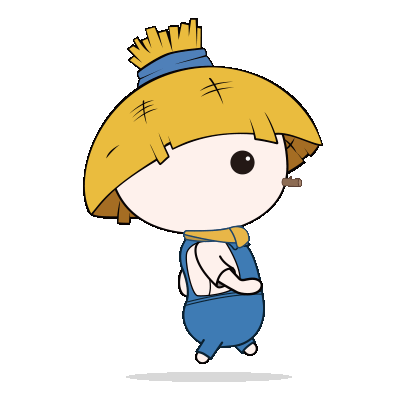去,更不会再带上谢敬丰浪迹天涯,因此也就没有理会他那吃人的目光。
谢敬丰原本以为,自己都能留在他身边了,自然也不会再次被他抛下,他还想着能够有朝一日感动他,让他放下成见跟自己回家,就算是不回去,至少,也不要带着对他们的怨恨一辈子,可是,他现在就居然开始打了跟他分道扬镳的主意。还说什么不是一路人?跟他都不是一路人,那他究竟跟谁才是一路人?这些江湖人吗?可他也不是无家可归啊?他并非需要浪迹江湖,他是天潢贵胄,怎么可以跟这些人一起流落在外?
他是不愿意回家,却也不愿意再让自己留在他身边,而自己分明也没有做错什么,却还是没有得到他的一丝待见。
他不禁想,他究竟是有多厌恶他们,才会这么云淡风轻的说着如此恶毒的话。
他心中委屈,他以为找到了次兄所有人都会开心,可如今,他却不愿意跟他们成为一家人,他的次兄也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的次兄了,就像他们说的,物是人非,人心易变。
一顿饭就在两兄弟无声的对峙下悄无声息的结束。
谢敬丰固执的不肯让谢文文如愿,想让他离开,除非是天塌了。
冬天的白天很短,吃完结束天色就昏暗了,谢文文抱着胳膊站在屋檐下,头顶的灯笼随着风一晃一晃的,地上他的影子也忽大忽小。他注意到了从那损毁后的池子里出来的白行云,尽管衣裳半扎在了腰上,可还是打湿了一点,这么冷的天他居然敢脱了鞋下水,出水的时候在原地蹦了几蹦,似乎是等回了暖才穿上鞋。
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从水里翻出来的,是王令嗣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的那剂药。
白行云知道谢文文在看,也就没有避开,大方的朝他走去。
两个人一人站在廊下,一人站在台阶下,原本会比白行云矮了一点的谢文文也高了他两个头。
白行云看向他的时候需要抬起脸,足够让谢文文看清他硬朗的棱角。
他朝着灯下的那抹长身玉立而去,张开手心,问:
“这是什么?”
谢文文看着那在灯下泛着光斑的瓷瓶,不语。食指点着肩膀,一下没一下的,神色晦暗不明,叫人很难猜。
许是他们这段时日发生了太多难以意料之事,经历了几番周折才重聚,白行云如今对谢文文格外小心翼翼,总有种呵护备至在其中。
担心他误会自己背地里盯着他,遂解释:
“我不是故意盯着你们的,我当时只是提防他,毕竟他不安全。那时候离得远没有听清你跟他之间的对话,我只看见了你摔了东西进池子里,看出他似乎很紧张。”
他想,王令嗣那般重视此物,都不惜天寒地冻的跳进池水里去捞,可惜是白费功夫,但足以说明此物的重要性,于是他趁着饭后无人就下了池子去打捞,原本也只是试试看,结果果真还就叫他捞了出来。一个普通的瓷瓶,沈胥那里多的是这样的瓶瓶罐罐,平日里用来装着药剂,只是他不知晓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寻常之物,是而才会问起谢文文。
他想,谢文文定然也是知晓的,只是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他不喜之物,是而才会丢开。
看着他手心里摊开之物,谢文文挑眉,昏黄的灯火下,脸上绮丽又透着一股狡黠。
“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白行云依言打开,瓶口是塞着木塞,但禁不住溢进去水,泡了一下午的水,如今瓶子里面已经空空如也,有的也就底部的一点水渍罢了。
白行云只觉得奇怪。“空的。”
谢文文在心底叹了口气,说没有一点触动是假的,曾经也好歹期望过活过,也贪婪着人世间的烟火美好,期待着能够跟自己的意中人白头偕老,但如今,算是被他自己彻底的绝了后路。王令嗣也是个狠人,怕是无药山庄如今被王令嗣折腾的够呛,亓官云前功尽弃,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临危受命的武林盟主。
掩过眼底的黯然,他只道:“因为遇水则化,没了。”
在他抛开的那一刻,他就没想过让这剂药成为他的束缚,自然也成就不了他的希望,如今亲眼看着里面空空如也,他还是有瞬间的失落。
宋元昇不惜掷下千金,也亏了亓官云半年的努力了,功亏一篑。
如今自己这样,还是认命吧。
白行云瞅着谢文文的神色,模糊不清,隐隐约约觉得不对,还是问出了自己心底的困惑。
“那是什么?毒?还是药?什么药?”
他猜的很准,这瓷瓶里装的一定跟药物有关,不然也不会叫王令嗣当时那般惶恐。
可面对避而不谈的谢文文,他只能够猜。
天色愈发的暗淡,映在两人脸上的烛光也越发的明亮,沉默的谢文文思考了半晌,才施施然道:“是诅咒。”
这句话说的跟玩笑话似的,可也的确就是玩笑话。
白行云自然是不信的,从他此时的神情就足以看得出来。
谢文文问他:“你信吗?”
白行云认真的看着他,点头。
“你说我就信。”他眼底的郑重,好似不论谢文文往后说什么,饶是离经叛道、天马行空的言论他都要信了。
谢文文知道他分明是不信的,可还是会说信。此时,心底似乎有什么暖流涌出来,四面八方的包裹住了他,让本还失意的他得到了慰藉。
天上的月亮不怎么明亮,许是暗沉的乌云太密集的缘故,两人就这么站在外面吹起风,听着灶房里的火烧的噼里啪啦。
他能想象的到,此刻刘小天他们几人围在了一起烤着炽热的火,或许有压低了声音谈论他。
四周静谧,鸟雀声也无。
“竹林外面是什么?”
他住在这里至今都没有出去过,整日里围着这座屋子转悠,约莫是被困在一个地方太久了,总是会向往这方寸之外的地方。
他或许是矛盾的,向往自由却图安宁。
“还是竹林,这整个山头都是南竹。”白行云柔声回答,同他一道幽幽的望着林子之外的那一圈灰暗。
他想,经此一事,纵然一波三折可总归会太平了,不会再沾染上不属于他们的风波。
能安定下来,才是他们的夙愿,他们不属于这里,也不适合权利党争的争斗。
“我小时候读过一本民间话本,里面就描写了一个长居深山竹林的仙人,他有一日突发奇想,想要下山体验民生疾苦,于是义无反顾的下了山,在人间过了四季,沾染了烟火气,就当不成神仙了,结局的最后,是他变成了一个清苦的老人,靠着编织的手艺过活。”
白行云不知道谢文文是想表达什么,也就没有接话,后来,就听到他压着声音但依旧能叫人听出其中苦涩的话。
“真可悲,好好的神仙不当,偏要去做个可悲的人。”
他应该不是仅在讲一个儿时读过的故事,可难在白行云并非心思细腻之人,无法意味出他所言的涵义。
这时候的白行云就有些羡慕沈胥了,如果是他一定就能读出此刻谢文文心中所想;他又羡慕小茶,陪伴了他的过去,知晓了他的曾经,一定能知道他在难过什么。
他并非自谦,其实,曾经的自己更不擅长言辞,也是偶然间的与他们为伴,相约江湖,各取所长,深受感染才叫如今的自己看着不再如当初的沉闷,跟个锯嘴葫芦似的,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他所想,他也不知道别人所想。
今日听到他同谢敬丰说的话,白行云不意外,他知道谢文文终有一日会做出决定的,只是,他还是忍不住去想,他当真能够做到一身轻松毫不留恋的放下过去吗?
已经到了家门口,见过了家中人,他还能不留念吗?
可他的神情看着,并不受世俗所累,自在如我,好似超脱了一切,好似随时都可能消失一般。这跟他认识的谢文文不一样,至少,让人看起来,抓得住,留得下。
他浅淡的神情被灯火包裹,眼中,无悲无喜,忽然间,白行云心中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来,深想下去,谢文文就好似真的会化作一阵风烟,于世间消失。
他对于北境的羁绊释放的太从容了,这不该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从容。虽然他这些时日以来看似一如既往的轻快,还能跟刘小天打趣,与他们商议今后,可他已经从谢文文的眼中看不出一丝有恋世的情绪,他还是更希望谢文文能够像个正常喜怒哀乐的人,恨他所恨,喜他所喜,而不是如今这般,大恸之后,了无生趣。
他深吸了口冷气,使得脑子也越发清晰,抓着身上的布料,他意有所指的问:“你不想回去吗?”
“回哪?”谢文文淡然的神情叫他看不出他是否是明知故问,但他约莫是想了下,才恍然大悟道:
“噢,你说王府?不回去,我这人心眼小,做不出让自己难过的事情。”
又是这般,他表现的太过轻快,正常的反常,叫白行云忍不住担忧,是否是他多想还是谢文文已经走进了自己的死胡同。
谢文文转身看他,两个人原本是肩并肩的一同眺望,此刻却相对而视,他把白行云藏在眼底的忧色尽收眼底,而自己却逐渐的隐去了原本的从容。
他明白自己即使表现的太过寻常,可到底于他们来说像自己这样经历了大起大落之人合该表现出不一样的情绪来,可他太从容了,许是就对他们来说不正常了。
可要说让他表现出悲恸或者怨天尤人的神情来,还真有点难。
走到如今的这一步,早已经就埋下了隐患,况且,曾经的自己也不是没有把这些情绪表现的淋漓尽致,可那些时候,太失望了,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吧。
见到谢敬捷又见到谢敬丰,是他此行的意外也是收获,其实,见过了总比没有见过的好,至少,亲眼所见,他们都好好的,身康体健,幸福安乐。而他们,理当如此。
白行云皱眉,隐约觉着不对,可还是按住了那丝疑虑,他笑着同他道:
“那我们不日动身启程回灵虚派,我之前有写信给师父,此时怕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我们了,我们如果日夜兼程,或许还能在除夕前抵达。门派里人少,却也曾是天南地北聚来的,大家最喜欢在最冷的日子喝最热的汤,有滋有味的,你们去了可都要去尝尝。”
他像是摒弃了所有的杂想,认认真真又满怀期待的同他勾勒着未来的好景。
那本也是他们一开始的约定,然如今,却有人会食言而肥。
谢文文垂下眼眸,不去触碰他眼底的温柔,自从明白自己也会重新喜欢上另一个人开始,他的一举一动总是能叫他心神荡漾,生出一丝不能够的希冀来,他是怕了,就怕会沉溺在这样的温柔里,不可自拔。
说好的做兄弟朋友,而他却要误人子弟。
哪里能够。
而白行云是同宋元昇不同的,眼底看人的神色也不一般,他爱过宋元昇的权势威仪,以及他的雪中送炭和那像春雨一般的温柔,可如今,却还是会喜欢上另一个人的润物无声。
如果,如果说,他遇到白行云的时间不是在十年之后,该多好,起码,他也会学着去爱一个人而不轻贱自己,可怜自己。
但如今,好像都晚了,天都暗了,再次苏醒的黎明永远都不是昨日的。
谢文文捏着冰冷的指尖,鼻头微酸,身后是刘小天嬉笑的声音,一堵墙都抵挡不住的喜乐,心头不舍。
他轻声道:“此行一去,路途遥远,我就,不一道了吧。”
白行云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分明是能够知道答案的,却还是固执的去问:“为什么?”
为什么?谢文文笑了笑,约莫是天色昏暗的缘故,叫人看不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