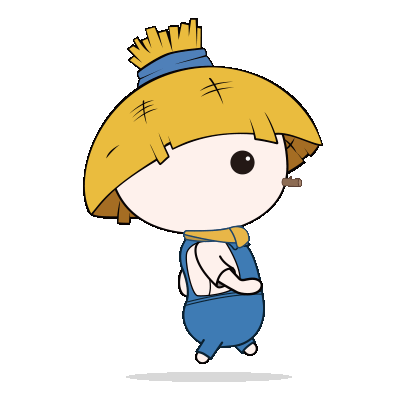沈宗良听后, 端着酒回了沙发上,架着腿说:“你们不晓得,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来, 说出来。”唐纳言旁边的长椅上一坐,“我们哥俩儿也听个乐子。”
沈宗良用拇指推开烟盒,大力扔了一支到他脸上。
那一头笑嘻嘻地接了,拨开打火机点燃,抽了一口。
“有个小年轻, 那模样长得挺标致,经济上嘛,也很有一些实力。”沈宗良点上烟,回忆起那天的情形, 不紧不慢地抽了一口,唉了声,“对她是晚上接,早上送, 笑脸相迎,甭提多殷勤了。”
唐纳言看他这副吃了败仗的样子,实在是忍不住不笑。
周覆上了酒劲, 摇头晃脑地质疑他:“都有个小年轻了,您还沉得住气啊, 够可以的。”
过了片刻,沈宗良匀缓地吐了两口白烟后,嘲弄地笑了笑。
他弹了弹烟灰,目光都盯在明灭火星上,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是连问都不敢问。”
“这有什么不敢问的!”周覆把酒杯往茶几上一摔,模仿沈宗良的口气说:“就大胆问啊, 那什么,小惠啊,他是你男朋友吗?发生过实质关系没有?”
听见这么粗俗的话,沈宗良登时拧紧了眉头。
他抬起眼皮,戏谑地看了周覆一眼:“平时程老师在家,会不会骂你是个下作胚?”
周覆笑,心虚地摸摸鼻子,“骂。她什么都骂。”
他了然地点头,“这就对了。”
唐纳言说:“你怕听见钟且惠说是啊?”
沈宗良摇头,“也不全是。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她就算谈上了恋爱,也碍不着什么事的。我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否则人都被她逼疯了,我也总要活命。”
听见坐上位的人抽着烟,心平气和地说出这样的疯话来。
周覆抖了抖肩膀,“啧,多少年没见你这样了,真他妈带劲。”
“是啊,你不能老这样。”唐纳言认同地点头,“这几年你都半隐退状态了,人也不见,什么局又都不露面。各方面稳定后,现在这帮新进京的小兔崽子,对你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天杀的,看我好说话一点,都跑来跟我打听。”
沈宗良灰心丧气地笑了。
最乱的那两年,任何的情况都不明朗,他深居简出,不肯过多地见生人,有自伤的原因在,但不都是。
韬光养晦,用而示之不用,是沈宗良站在变局的开端做出的应对,是他做惯了,也最擅长做的事情。
他把烟掐了说:“好办,下次你就说我死了。”
周覆:“这也不假。除了还喘口气,跟死了也没两样。”
“......”
过了清明的江城,晚风里还藏着寒意,扑在人脸上像落花拂面,份量不轻。
沈宗良没有待很久,会馆里笙箫管笛越吹越急切的时候,他心里发燥,讲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开了。
回宾馆前,他去益南路的小楼里看了一眼,已经收拾得很好,不日就可以搬进去。
长时间住在东郊宾馆,会给集团上下一个不良讯号,仿佛他是来这里做客的,连个固定居所都没有。尽管沈宗良此行的目的,实打实就是来表功过渡的,但该有的姿态必须拿出来。
他回房间的时候,碰上两个服务员抱着百合出来。
她们立刻站住,在走廊上站成一排,避了避,低头问好:“董事长。”
沈宗良打量了一眼,这个花瓶依稀是摆在他床头的那个。
他指间夹着的烟还冒着火光,问了句:“怎么回事?”
“噢,是这样的。”其中一个女服务员说:“钟主任走之前,她提醒我说,不要在您的床头放百合,尤其是封闭的室内,它的气味会让睡熟中的人头痛。”
沈宗良心下微动,面上还是那副冷淡样子,“去吧。”
人走了以后,他等不及般地抬起烟,递到唇边吁了一口。
沈宗良在烟雾袅袅里笑了下,这头小白眼狼还是在乎他,没有完全泯灭了良心。
他大步进了室内,窗帘大开着,人间万万里都在灯火里浮现。
因为一盆开败的花,沈宗良起伏了一晚上的心情,似乎又好转了。
他站在露台上,平静镇定地抽完这支烟,凉风吹过他的肩膀。
所以说,爱并不是在不见面的日子里就停止了,它会野蛮自由地生长。
沈宗良拿出手机来看,小惠应该是到了家,也忙完了。几分钟前,她朋友圈转发了法制期刊的一篇,关于物债两分的历史争议。
他想起住在胡同里的时候,因为家中有个学法律的小女孩,时常被迫听见一些学术界讨论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个物债两分。
沈宗良记得那天,他摆弄起了很久不练的字帖,写得认真的时候,小惠是从桌子底下钻过来的,她年纪尚小的时候,总是花样很多。
对付他就像随手扔掉包里多余的试卷一样轻松。
她汁水淋漓地吃了他一阵子,弄得他呼吸都乱了,手腕密密麻麻地抖起来,墨水在宣纸上化成一个粗陋的疤点,对他这种收藏家来说,简直不忍相看。
沈宗良把她抱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压在桌子上吻,吻到嘴唇都合不拢,那个时候她目光**地,摸了摸唇角,肆无忌惮地望着他,“不能轻一点吗?”
他的唇压过她薄脆的耳骨,“那你呢?毁了我花大价钱买的字帖,又怎么说?”
小惠的声音带着很黏腻的娇气,“小叔叔,你坐得太直了,这个位置我有点儿吞不进去,下来一点,再吃一会儿好不好?”
“不许。”沈宗良一把将她揉到身上,在摇晃的灯光里把她剥干净,本能地用力挺腰,“你的小嘴太能捣乱了。”
他那条昂贵西裤最终被丢进了垃圾桶,上面浸饱小女孩气味暧昧的液体,像婴儿在口欲期频繁更换的口水巾,完全没办法再穿了。
且惠洗完澡,乖巧地躺回他的怀里,学着教授振臂一呼的语气对他讲:“现在主流观点还不是物债两分,人大也不主张,但是没关系,孩子们,人大一年才毕业多少人?咱们一年又培养多少人?总有一天,法学界会是物债两分的天下!”
后来,沈宗良翻着最新颁布的《民法典》,总体上还是采纳了物债两分的体系,也在实践层面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但那一晚笑着跟他说这些的小姑娘,他已经看不见了。
沈宗良关了窗帘,单手解着衬衫走进浴室,水温调到冷水那一档,站在花洒下冲了很久,出来时,浑身挂满了冰冷的水珠。
像冬天的早晨,孤孤单单地立在路边,一棵披满霜雪的白桦树。
他没急着擦干,裹了一条浴巾,撑在洗手台上喘了很久,水从下巴上滴向地板。
以往洗完冷水澡,骨缝深处那股燥动危险的热度会下去很多。
今天怪了,是因为这个房间里弥留着她的味道吗?还是她坐得太近了?
沈宗良烦闷地扯掉浴巾,又把自己重新洗了一遍。
不记得是谁说的,人一旦太痴迷于回忆,并非什么好兆头,但他要是连回忆都没有了,还能有什么呢?
四月底的一个周二,刚开完总部的合规会议,且惠拿上记录本,也没回办公室,直接去了职工食堂吃饭。
她从消毒碗柜里拿了餐盘,从窗口递进去,“麻烦阿姨,帮我打一下饭。”
“今天这么晚来吃饭啊?”阿姨笑眯眯地接过去,“菜心吃不吃啦?”
且惠说:“吃的呀,总部开视频会,领导都饿着肚子讲话呢,我们怎么敢催啊。”
“那阿姨给你多打一点。”
“够了够了,多了我也吃不完,浪费。”
她端着饭走了两步,看见靠窗的桌子上,一道峭拔的背影。且惠没再往前走,离了他三四桌远的距离,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来吃。
前阵子听见部门里的人议论,说沈董亲民得很,都不单独开小灶,中午就在员工食堂用餐,碰上了还会和大家坐一起,说说话。
且惠连手机都没玩,想着抓紧吃一吃就去午休,免得撞上沈宗良。她喝了一口汤,抬头时,看见食堂进来一个人,穿着休闲,踩一双限量款的球鞋,手里提了个纸袋。
她紧张地动了动唇,想出声,但喉咙绷得太厉害了。
“且惠!”王秉文一下就在空旷的食堂里找到她,“你怎么还没吃完饭呢?”
他这嗷叫的一嗓子,让前面安静吃饭的沈宗良也回过头,一脸的阴沉不悦。
且惠真想把手边的保温杯举起来,挡住脸。
她干涩地开口:“对,我开会开晚了。”
王秉文拉开椅子,把东西都放下,“我下午就要出差了,给你买的下午茶。”
且惠尴尬得脸都红了,她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谢谢。不过我好像跟你说过,我没有吃这些的习惯。”
他还是笑:“那我总不能空着手来,你不吃,分给同事也好啊。”
且惠不想再纠结于饮食习惯了,尤其前面还坐着一个沈宗良,只隔了这么远,他们说了什么很容易听清。她呃了一下,“这次是去哪里出差?”
王秉文说:“纽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要去半个多月。我想等我回来了,你能不能去我家吃顿饭?我爸妈说想见见你。”
“啊?”且惠惊得张大了嘴,匪夷所思:“你爸妈为什么要见我?”
王秉文安慰她说:“你别那么害怕,我在你家做客那么多次,董老师每次弄一大桌子菜,我爸妈讲究礼尚往来嘛。”
且惠松了口气。她忽然天真地冒出一句:“那你应该请董老师吃啊。”
“哈哈。”王秉文忽然大声笑了,“且惠你好幽默。你要是喜欢,当然可以叫上老师一起,我欢迎。”
她抿着唇,沉默地低头把菜夹进嘴里。
这很幽默吗?本来就不是她的人情,实话实话而已。
面前的阳光被挡去大半,又很快晒过来。
且惠抬头看,原来是沈宗良打面前过去了。
他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扔进池子里那一下,哐当一声巨响。
且惠浑身抖了一下,沈宗良用那么大力,像掼在了她的心上。
王秉文浑然未觉,“你先答应我,可不可以?”
她混沌地笑笑:“我最近很忙,而且见父母这种事情,好像不适合我们做。”
他怀柔政策地说服她:“不是见父母,是去我家做一次客而已,我们不是正在相处吗?”
且惠摇头:“王秉文,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没有在和你产生任何关联,你是我妈妈的学生,她很喜欢你,仅此而已。”
王秉文还要再说,且惠放在桌上的手机震了震。
她抬手,示意他先等一等,“关主任?”
关鹏说:“噢,小钟啊,沈董要看上季度的合规材料,你现在拿去他办公室吧。”
“现在?”且惠看了一眼时间,这也太着急了吧。
他是铁打的,午休时间都要用在工作上呀。
关鹏很确定地说:“对,就是现在,他立等着要看,那有什么办法,你辛苦一下。”
“好吧。”且惠合理怀疑他在没事找事,“我马上过去。”
王秉文站起来问:“没什么事吧?”
他永远都这样,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对于类似拒绝的话,总是充耳不闻。
但今天且惠没时间再说了,她收拾了一下,“不好意思,我要去工作了,你一路平安啊。”
“嗯,那等我回来再找你。”
且惠唉了一声,没接这个话,步子轻盈地走开了。
她先回了办公室,把相关的文件都找了出来,抱着档案盒上了八楼。
董事长办公室里的百叶窗帘都打了下来,灯也没开两盏,昏昏暗暗。
沈宗良往后靠在转椅上,沉闷地抽着一支烟,零零星星的火光照亮他高挺的鼻梁。他紧皱着眉,仿佛抽得很痛苦。
对,就是痛苦。
且惠脑子里冒出这个词的时候,她和自己再三确认。
他都从那么险恶的局势里挺过来了。
沈家非但没有失势,反而受了极高的嘉奖,他是在苦什么?
且惠腾出一只手来敲门,“沈董。”
隔着缭绕的烟雾,沈宗良盯着她看了老半天,微眯了眼,像是看不清来人的样子。等且惠快坚持不住,手里的东西东倒西歪了,他才说:“进来。”
且惠把材料放到了茶几上,轻轻喘着,“您要的,上季度的合规文件都在这里了。”
沈宗良在她惊疑不定的目光里走来,到了门边,利落地关上,反锁。
她看着他这一通动作,局促地站在原地,“为......为什么锁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