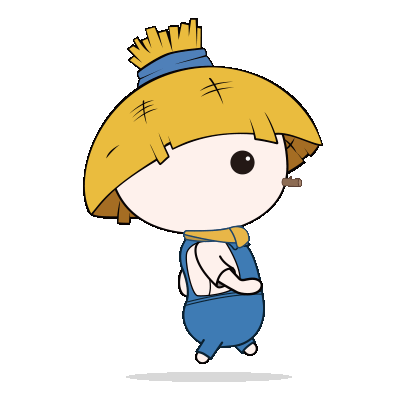忽然接到妈妈电话时候, 且惠正在图书馆里写论文,外边是湛蓝的天,寥寥有几朵白云, 天地之间全是澄明。
她从一大堆资料里抬头,心中隐隐不安,明明前天母女俩才打过电话,按常理,董玉书不会和她联系得这么勤。
且惠轻快地喂了一声, “妈妈。”
董玉书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她说:“小囡,我在外婆的这栋老楼里,门锁密码多少?”
她有点吓到, 慌乱间差点报错,“256......不是,258712。”
董玉书开了门,说:“好, 你下了课就回来,妈妈在等你。”
且惠握着手机愣了很久的神。
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妈妈会突然过来?都没有知会她一声。
何况外婆那里, 她自己都很久没去住过,家具都盖着一层防尘布, 妈妈一看就要露馅。
她没敢耽误,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背上书包走了。
且惠连方伯也没敢叫,自己搭地铁回了家。
董玉书手脚快, 已经把这儿收拾的差不多了。
且惠进门时,她拍了拍手上的灰, “啪嗒”一声,扔过来一双拖鞋。
她悻悻地换上,靠着餐桌把书包放下,“妈妈,你怎么过来也不告诉我,我好去接你啊。”
董玉书给她倒了杯水,“不用,我在京里工作生活了十五年,比你熟。”
且惠接过来喝了口,眨着眼,不安地问:“您什么时候到的啊?”
“上午。”董玉书继续擦洗着桌子,说:“先去见了字真,还有你男友的妈妈。”
董玉书是坐高铁到的,冯夫人去接的她。早在去江城出差时,二人就已经碰过头了。
她走了一段路才出来,有点热,特意挑选的长裙料子不透气,被汗黏在背上。
反观王字真,站在车边,只穿了件白衬衫和蚕丝裤,松弛得体。
董玉书想起那些年的酒局,她们光鲜地坐在各自的丈夫身边,闲闲聊着养女儿的心得。至此相交,已近十八载。
岁月在每个人身上的着力度相去甚远,十八年过去,王字真始终如初成少妇时一般,保养得宜,笑容和善。再看看她自己,风霜添鬓,因为长年累月的操持,已经有了老态了。
王字真接过她的行李,“玉书,一路上还顺利吗?”
董玉书笑笑说:“还好。多年不出远门了,还真有点累。”
王字真考虑了下,“那我送你去酒店休息,孩子的事过两天再说。”
“来一趟就是为了她的事,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还是走吧。”
王字真让她先上了车。
在江城出差时,也是董玉书自己找到酒店来的,问且惠的近况。
她不是多事的人,也怕她们母女因此大闹,替女孩子遮掩了一下。
但董玉书来意明确,直接就问:“且惠是不是和沈家的在一起?我以前的老同事跟我说,在西平巷里看见她,进了沈家的门就没再出来,好几次都是这样。”
王字真支吾了一下,“玉书,她二十岁了,不是小孩子,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的,我们当妈妈的,也不必要管那么多。”
董玉书摇了摇头,“不要怪我说话难听。字真,沈家的门槛高得吓死人,就是她爷爷在世也攀不上的,她又拿什么去处理?沈家老二大她那么多,她被人哄骗了都不知道,他们那种人哪有什么真心的,我不信他还能娶我女儿。”
一时间,王字真也没话好讲了。
换了是她在董玉书的处境,丈夫死了,她费尽心血养出一个漂亮听话又上进的女儿,现在大学还没毕业,就搅进了沈家这个深不见底的旋涡里,结果是不必想的,未来也不用谈,只有白白虚掷年华的份,也许还要把名声搭进去。想想她就要急死了。
从江城回来没两天,沈夫人又找上了她,让她请董玉书进京,说有事商量。
王字真和她说了,语气尽量的云淡风轻,说你不愿意的话,我想法子给你推掉。
但董玉书说她要去,关乎她女儿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不要紧的。
这场会面很短,沈夫人是从贵太太们的牌局上临时出来的,没说几句就结束了,对于董玉书提出来的,安排好她女儿在牛津的学习和生活,沈夫人甚至感到不安,就这个未免也太简单了点。
但董玉书只是笑了笑,她讲,说了您也不会明白的。
这世上没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女儿。
董玉书相信,且惠一定是在沈宗良身上得到了她缺失很久、渴望很久的东西,这个年轻的子弟才会这么打动她。
她不是轻易能够袒露自己的人,在江城上学时,全班同学都很喜欢她,但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从小到大,她要好的女朋友也只有幼圆。
虽然且惠没跟她说过这些事,但她也能猜到几分,大概就是怀着一种舍身成仁的悲壮,一天天的和他混在一起。等谈不下去了,就好说好散地离开,所以她认为,完全没有让家里知道的必要。
所有的蛛丝马迹汇合成一点,也不过就是三个字,她爱他,非常爱。
既然如此,以且惠那样淡泊的性子,就不可能和他做什么交换,被心爱的人看轻,这比杀了她还要难受。
但是女儿不提,董玉书不能不提,她独自挺过的这些年,看了那么多的白眼,就只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能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不去争取,是要悔青肠子的。
董玉书提了,但也只敢提到这个程度为止了。
这已经是拿她们的母女关系在冒险。她能猜出且惠知道以后的反应,一定哭着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把她变成一个势利小人。
就像现在这样。
董玉书坐在她对面,很冷静地跟且惠说完她见过沈夫人后,她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眼泪缀在她的睫毛上,像秋天丁香叶上的水珠,就快承受不住重量,要掉下来。
她颤抖着嘴唇重复,“你跟他妈妈说,要她支付我在牛津的学费和生活费?还要她找校长写推荐信?”
董玉书说:“这对她来说,就是一笔小钱而已,但累死妈妈都赚不到。”
且惠嚯地一下站起来,“那我可以不去牛津上学啊,我能接受回江城读研的。”
“但我不能接受!”
董玉书猛地摔下手上的抹布,扬声冲她喊。
那些没落下的水珠瞬间汇成了小河,从她的脸颊上流淌过去。
且惠哭着瘪起了嘴,“你让沈宗良怎么看我!为了一个破学校,你叫我在他面前抬不起头!”
“才不是破学校!钟且惠,这是一份顶尖的学历,它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东西,比那些你放不下的尊严和骄傲,要有用的多!你还年轻,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等将来他沈宗良抛弃你而另娶一个姑娘,再也不记得你是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我为你做了这样的选择!”
且惠紧接着就喊了一句,“这样的选择就是让他认为,我接近他,说爱他,全部都是有目的的!”
她根本没有余力去想牛津这张毕业证的威力,满脑子都是关于沈宗良。
且惠觉得天塌了,她在他那里彻底成了个罪人,一滩污泥一样肮脏。
真是小孩子爱说胡话。
董玉书因为她感到可笑,“你要自己在他心目中那么完美无缺干什么?是想他在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里,一想起你就长吁短叹,遗憾得不得了?还是每次看见他门当户对却毫无情致的妻子,都能记起你的好?”
“妈妈!”且惠捂着耳朵尖叫起来,“你不用总是强调门当户对,我知道我和他门不当,户也不对。”
董玉书毫不留情地吼回去,“知道你就给我消停一点!不要再发神经了。我还没有跟你计较你骗我的事情,你反倒蛮横上了。你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只不过问他们家讨了一点东西,你跟我凶什么?妈妈一个人把你养这么大,难道我错了吗?”
回回都是如此。
每次且惠不听话了,不肯采纳她的意见了,她就要搬出恩情来压她。仿佛这是一道免罪金牌,因为她含辛茹苦地供养了她,就可以为她做任何决定,哪怕是错的,也应该被赦免。
以往的很多次,且惠都会在这句话里沉默下来。
然后擦擦泪,说我回房间写作业了,这是她妥协的表示。
但这次且惠没有再这样。
她隔着一张长餐桌和妈妈对峙,尖起凄厉的嗓音说:“你问他们家讨东西,还不如让我从楼上跳下去!”
董玉书抖动着面庞,她不敢信,不敢信她一向温和的女儿对她这么说话。
她眼尾酸得溢出水花来,颤声说:“钟且惠,你不要搞错了,我是为你好。女孩子只有学历和事业是靠得住的,男人你就不要想了。”
且惠仍倔着脑袋,“您不要混淆概念,我什么时候说要放弃学习了?也从没有想过靠沈宗良,但您不应该这么独断。”
“是,我独断。”董玉书有点喘不上来气,捂着胸口坐下,指了指门外,“那你现在去告诉沈宗良,都是你那个功利的妈出的主意,你还是清白单纯的。去吧,赶在他妈妈和他笑话你之前。”
她听后,哭起来委屈得更厉害了,“我怎么可能那么说!”
看董玉书脸色越来越苍白,且惠泪眼婆娑地,跑到董玉书身边,“妈妈,你没事吧?”
她紧皱着眉头,戳了一下沙发上,“我包里有瓶硝酸甘油,你帮我拿来。”
且惠擦擦眼泪跑过去,手忙脚乱地把东西全倒出来,找到了药又跑过来。
董玉书倒出一片来吞下去,靠在椅子上闭目不语。
且惠守在身边,“妈,我扶你去床上躺着吧。”
她摆摆手,“不用,最近有点心绞痛,吃了药就好了。”
“你以前也没有这个毛病啊。”且惠握着她的手问:“是不是教补习班太累了?”
董玉书说:“知道你的事情以后,我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你说呢?”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且惠的声线软了下来,“而且,我都打算了要和他分手。”
董玉书反握住她的手,几乎是苦苦哀求,“既然要分手,那你就听妈妈的,不要那么在乎他了,好不好?”
但且惠还是没松口,“不说这个,我先扶你去床上休息。”
“我不去!你也不要扶我。”董玉书一下子又推开了她,“你不肯去国外读书,我的死活你就不要管了。”
董玉书颤巍巍的,扶着桌子站起来,去收拾客厅里的行李箱。
且惠吓得要命,不知道她这是要干什么。
她小心地在后面跟着,“妈,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好吗?”
“不用了,你给我买张高铁票,直接送我去坐车,我回江城。”
且惠气得直跺脚,“你这个样子能去坐高铁吗?”
眼看董玉书越来越不好了,她还要蹲下去开箱子,“那就不用你操心了,死生有命,你记得别把我和你爸埋在一块儿,我没脸见他。”
“好!”且惠咬咬牙,赌咒一般:“我去读,我去读行了吗?”
董玉书这才停下手里的动作,“到沙发上躺一下,妈妈好难受。”
且惠不敢再耽误了,赶紧打了120。
拨键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脑子里都是爸爸过世时那副可怕的场景。
她倒来一杯热水,跪在沙发边,“妈,你还能喝得下吗?”
董玉书摇摇头,声音微弱地说:“小囡,不要怪妈妈,好不好?”
眼泪再一次堵满了且惠的嗓子眼。
她也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拼命地点头。
救护车是过了二十分钟才到的,说这里太难开进来了。
到了医院,且惠一直陪着董玉书,一步都不敢离开。
直到护士拉上帘子说:“好了,这里有医生做检查,你先去缴费吧。”
且惠再三地确认,“我妈妈没什么事吧?”
值班医生说:“目前没什么问题,具体的要做过检查才知道。”
她点点头,拿着一迭交费的单子,麻木地走在过道里。
身上带的钱不够,且惠从包里找出沈宗良的卡来应了急。
他那张黑卡从窗口里递出来的时候,且惠接回来,垂低眼帘,手指摩挲在他烫金的拼音上,心头涌上一股巨大的、难言的酸楚。
她本来还想在冬天,好好给他过一个生日的。
上一次他人在出差,隔着屏幕说生日快乐,仪式感全无。
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个机会了。
得了沈夫人的好处,还要赖着人家的儿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且惠这么想着,浑圆的眼泪宛如珍珠落玉盘,砸在了黑色的卡面上。